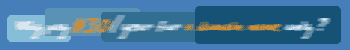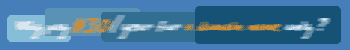巩平撂下电话,坐在沙发上,拿起积累多日的报纸。人民日报他总是后看,通常也
只扫一遍标题。他有一份大参考和几份境外的报刊 -- 平常百姓是不能看的,他不
觉得有什么不公。工作需要嘛,比他级别还高的还有别的花样呢,难道人人都去看
国安部的文件才算公平?中央情报局的东西美国总统也不能随便看的,他敢抱怨吗?
免了你,尼克松就是榜样!
他给老同学透露内部消息也不能算不公平。说心里话,谁没个三亲六故?如果儿女
不争气,或者高考临场发挥不好,或者有病有灾的,难免不去求别人。中国国情使
然,过了这村谁知还有没有这店呢?多少有些节制,别太明显,太过份,引起太多
非议,引起太大民愤极大就是了。他很瞧不起那些不学无术、投机钻营,自视根基
牢靠,有恃无恐的家伙。他们所长就是那样。不过那样更好,要不了多久就会垮台,
自己扶正可是指日可待。时代毕竟在变嘛!
他懒懒地翻着报纸,一条消息跳入他的眼帘: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 ... 考生
状告国家教委。有意思!他欠欠身,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官官
相护”、“民告官,打大板”之说,哪里打得赢,受不受理都难说。上联合国去告
还差不多,但联合国敢干涉中国内政吗?平心而论,他也很同情那些贫穷落后地区
的娃,也嫉妒那些生在皇城根下的崽。当初如果不在沈阳,凭什么报吉林大学为第
一志愿。论成绩也进得京城一流大学,就是心虚没敢比量。尽管去念了研究生,现
在仍然被认为是半路出家,身份不纯。
如果你在北京挤过公共汽车,你一定听说过这样的话:一上脚踏板,立场就改变。
它惟妙惟肖地描绘了等车人与乘车人的心态。巩平已经在车上了,还稍好点,有了
座位。你能期望他怎么做?让自己乘的公共汽车严重超员,受阻,以致抛锚,还是
让那些没上来的人等下一班车?数量有限,捷足者先登嘛。当年开放搞活,老邓不
也放弃了共同贫穷,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有今天的可喜局面?
想到公共汽车,巩平暗暗笑了。那司机,售票员就算勤勤恳恳,公公正正地服务,
车队调度让他把人卸下,立刻回公司,他们能怎样?端谁的饭碗听谁的调遣。自己
当年遇上多少次都记不得,总是耽误了事儿没处抱怨的。说到国家,省长、市长名
义上是民选的,实际还不是中央让谁当谁当,让谁下谁下!谁决定你的位置,你就
得向谁负责,冠冕堂皇地说别的也是瞎扯。还举老邓的例子吧,当年不跟老毛认
错,能当上常务副总理?这叫韬晦,也叫韬略。归根结底中国人是愚昧的,人民代
表也是白痴,西方那一套不适用。中国人需要领袖、领导、引导,就象当年德国人
一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京城晚景如画,比画还美。它是动态的,日新月异。汽车尾
灯划出漫长、蜿蜒的条条红线好似人体的血脉网络,通向全国各地,日夜不息地为
这古都输送营养,保持活力。巩平不须转身去看,他早已熟悉这一切。一切一切来
得都那么不容易,包括自己的家,自己餐桌上丰富的小菜,自己在所里的地位。他
从祖上的经历中学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如果不是帝王之才,那一定要跟对人。从
古之今,颠扑不破。没钱有钱,没权有权,要啥有啥。象老校友王安琪那种人,别
人唏嘘,他也唏嘘,心里却很是瞧不起,不识时务嘛。
妻子给他送来新茶,黑暗中也能看见她袅娜的身姿。巩平的心不由地动了一下,想
把她揽进怀里,但骤然亮起的电灯却冲得这个念头烟消云散。看着妻徐徐走进浴
室,他舔了下嘴唇,展开双臂放到宽大的沙发后背上,顺势头也仰靠上去。如果高
等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如果我是教委主任,该怎样处理它呢?作为一名学者,他
有其未泯灭的良知,而作为官方的御用文人,又有其不可动摇的利益立场。站在那
一边他都有精彩文章可作。过去当小喽罗的时候,摸不准领导意图,就写两份稿子,
左派言论放在左兜,右则右兜。现在当然不用这样了,只能为当政者出力,作一篇
足够了,难道真走眼了不成?
事情说来容易做来难,多少大人物风光无限,不小心就栽在放水上。那年杨成武跟
在彪帅后边高喊“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不知伤了谁,红得发紫没几
天就趴了。而刚刚爬起来的罗瑞卿大将怀着感激之心写文章,揭发红军时期林娃挑
唆后来倒运的彭大将军篡夺领导权,不想没几天大将军也正了名。真是天有不测风
云,地有变幻人心,实实的教训呐,教训!
浴室里传来哗哗啦啦的流水声把巩平拉回到现实,历史归历史,火烧眉毛还得顾眼
前才行。去年写的那篇文章立论本是不错的,论据却不够充分,犯了浮躁的毛病,
也怪时间太紧,部里催着发,以平息民怨。官方首肯是一回事,民间至今那来当靶
子的苦痛有谁知晓?还有那该死的互联网,整整把个大世界变成了小小的地球村,
想堵住人们的嘴巴几乎不可能了。老马识途,老马呀老马,你干嘛偏偏要说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至今,原食肉者密谋的政事,学者参与就很宽松了,
若草民都挤来插言,倒出来的不过是一堆浆糊罢了。
跑到国外的同学也全不顾情面。那个号称硬山果的家伙硬说我是强盗逻辑,拿着胶
棍打我的肋。开始还以为他吹捧我呢,心里正痒痒,要谢他一番,不想这会儿疼起
来。一个小百脸、戴副眼镜的渔夫化装成主持人采访我,明里套瓷,暗里欲剥我的
皮。还有个疯子更不像话,举手就扇我的脸,竟放言是用我自己的手。现在你们看
明白了,到底谁是强盗。我实无缚鸡之力,多少补品也无济于事,连一个娇若的妻
子都对付得吃力。再说,绊倒我有何好处?多半上来个更糟的。如果让我爬到教委
主任,副的也行,吉林大学总会沾些光的。
浴室的门悄悄转了个角度,浴衣里的躯体流光溢彩,徐徐飘来。看到仍在沉思的巩
平,妻子轻声说:“早些歇了吧,明天还要上班,身体 …… ”。“ …… 是工作
的本钱”,巩平默默叨咕道,“老一套,三十年过去,还是儿时的语言”。但他只
是笑了笑,“你先睡吧,有篇文章明天要 …… ”。望着妻悻悻离去的背影,巩平
心底默默涌出一丝歉意。他何尝不想象豹子一样矫健地扑上前,抱住妻的后腰,把
她举起,重重地甩到柔软的席梦思床垫上?何尝不想带妻子驾舢舨巡游大海,任凭
浪花飞溅,一忽儿冲上潮头,一忽儿跌落谷底 ……?
逝去的青春岁月是那样匆匆走过。城市 - 农村 - 大学 - 研究所,而学 - 而
立 - 不惑,下站该是“知命”了吧?象许多学者一样,他常常用孔子的话自勉。
翻翻日历,生命循圣人的足迹已走过半;看看业绩,万不如一。唉,人生如梦,转
眼就是百年呐!巩平自幼勤思好学,唯亲其体弱多病,在中小学每被人欺笑。他最
羡慕的英雄是武松,堂堂一表,凛凛一躯。下乡后他拼命干活,希望通过锻炼变得
强壮起来。他未能如愿以偿,意外收获是赢得了一位蒙古族少女的爱。这爱让他热
血沸腾,让他刻骨铭心。
在大学里,从晓燕温情脉脉的目光中他也读到过那种情感,但无论如何不能背弃以
身相许的“妻”。他实言相告,晓燕喜其直率,遂成亲密的异性朋友。晓燕出生于
书香门第,在他父亲这一分支上数五代,或为医、或为师;也有博取功名者,不贫
穷,亦不富贵,颇得乡民的敬重,一直保持着先生的称号。到划分“成份”时,
地、富、中、下、贫皆不宜,弄了个自由职业者。晓燕从小受着文史哲的熏陶,常
能出口成章,下乡时当过“土记者”,她所在的生产小队、大队都由她的文笔在公
社广播站风光过。报考吉大数学系只为听从父亲的劝告。当了多半生教授,治史之
严俨然国内一流大师,却沉重地对自己的子女说,“你们不要搞社会科学”。她理
解父亲,大学毕业后一直沿着专业方向前行。
(待续)
9/2/2001
 [可怜天下父母心]
--:老椰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老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