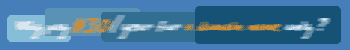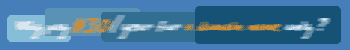五月二十四日,晴,礼拜五
进了机场拿了登机牌,一看表我就拍了自己脑门一下,提前两小时进站,创我乘美国国内
飞机的纪录。与吴霞商议订票是怎么埋怨她的,“二十年都过去了,至于急几个小时?订
那么早的票,太不酷了。”原来下意识里我也不酷,何苦那么早来?两个小时加飞行三小
时,无聊透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二十年一晃而过,其中有几个日子可以记得?昨天
几乎与前天一样,前天几乎与大前天一样,日子就那么单调,繁琐,枯燥。或许在这聚会
的三天里,会有值得记忆的时刻?
从飞机上看Houston,平淡无奇。飞机早二十分钟着陆,干等了十分钟才有gate 给我们放
行。走出这个安检,是这次旅行的转折点。出来远远就见高高的伍炯如,还有吴霞。吴霞
向我迎面走来作悲喜交集状,我发现自己却毫无控制地笑得象个白痴。回头见伍大侠竟然
拎着一套蓝子,“这是什么新式武器?”我忍不住问。他笑道,“拿几个篮子来讨饭吃啊。”
“你挎篮子太对不起观众了,篮子给我,你去给吴霞拎酒。”接过篮子来细看,又一次为
老伍寂默的雅致而惊奇。我们找到租车处,那儿竟排长队。趁伍大侠很绅士地把活儿都揽
去干时,我拉住吴霞细看,旧友重逢,八四年九月十七日天津一别,几乎十八年,她是有
点儿变了,又没有变,总而言之,从未出阁的小姐变成了少奶奶,“你呀,扒了皮我认得
你骨头!”
租上车我们开上了59号向彭华家驶去,真爽!诸位可还记得我臭名远扬的time machine,
我并非天真到真指望会回到大学时代,此时故知行车于他乡,难道不算time machine?老
伍轻车,吴霞熟路,我在后面浮想联翩,往事如飞鸟一样扑来。几乎整整二十年前,一九
八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有一次无情烈日下的三人行,是吴霞,我和滕秋克,坐电车从同
志街到火车站,吴霞不是在当电灯泡,他们俩送我回家奔丧。火车一动时,吴霞泪如雨下,
此情此景我终生不忘。吴霞丧父时,那些十二月里天短夜长阴暗无雪的冬日,她两天没上
课我和于洁坐电车去看她,路上于洁还笑谈说这丫头是不吃多了。到了她家见许多人许多
车,于洁脸色一变转身就走,我俩在街角站了好一会儿才鼓足勇气去敲门,吴霞出来抱住
我们哭成一团。家庭的变故多年后已成往事不再悲伤,更何况,吴霞,于洁和我又有多少
快乐的三人行。岁月无情,昔日不再来。时光改变了我们的外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梦
想,甚至于我们的记忆,但我想到大学时代,就不能不想起大学同学。我们曾从五湖四海
混到一股生活的洪流之中,也曾快乐同享,忧愁共担,也曾勾心斗角,争喧夺宠,汇成我
们五年的缘份。
吴霞识途,没费周折就到了彭华家,彭华,侯慧已在门口等候。进了彭华家门,见侯慧已
为我们准备了盒饭,早上一杯咖啡到此消耗怡尽,四五个小时的旅途置于脑后。吃着中国
饭,加上老同学的陪伴,一阵久违的温馨,让我觉得恍惚如梦中,如同回到一个遥远的家。
彭华去接了张红缨来,我一见她就忍不住动手动脚,拍肩膀揪头发,“老同座,你可没怎
么变,头发短了,见识长了。”红缨笑容依旧。彭华则诉苦:“在机场的老美,接到人不
是被啃就是被抱,可我连蚊子都不肯来光顾。”他连拥抱也没得一个,又得去接大队人马。
吴霞说要接大鸣,欲弃我而去,我说也要去,彭华则不许。我只得随遇而安。他们走了,
田洁虞伟来了,彭华没捞着的红缨的拥抱,虞伟却得到了,大家一番寒暄,而后就去了餐
馆。
到了餐馆就开始了无尽的等待,我生平最恨等人,如果有本好书,也还有几分“你爱来不
来”的潇洒,这天我手无片纸可读,等的一干人中有对我曾至关重要的陈阳;有我第一个
认识的大学同学朱大鸣,八四年十月十六日北农大一别至今;还有我一直为其聪明才智而
五体投地的支本欣禹阿东;等的我心力交瘁。好歹大家团团坐定,不巧正坐彭华边上,他
一而再再而三给尚在路上的孙宏为打电话,恬噪不休,我想此番我要死矣。强打精神拿出
朱大鸣和陈阳81年签的和同,为我们大学毕业后工资多少而打的赌据,传阅后田洁提出疑
问,说十好几年恐怕无效,彭华则说中文契约终生有效,只没人觉得好笑,丧气,扫兴,
没凑成趣让我白费心机。我为自己宽心,想他们谁输谁赢买了好吃的也没我的份,我管他
们的闲事。终于孙宏为到,好似第二只靴子丢了下来,总算可以放心了。曹宁君明天才来,
真真好老弟,晚来一天,救我好些细胞。
大鸣在饭桌上就歪脑袋打量我,打量完了也没说什么,我那本家变深沉了!等到了彭华家
她拿出她出版的书“多彩的美利坚”送我们,我悲喜交集。悲的是这么多年她没理我,原
来自己找到好玩的了,喜的是我早就知道此君不凡会有一番作为。我们一致要作者签字,
大鸣欣然提笔。至于我让大鸣签的什么,绝对不能让人知道,那句中文大大的不通,有损
我文人形象。
真难得,我们又能在一个屋顶下住一回,就寝时一论资排辈我和吴霞就滚到地上去了。女
主人很周到,地上也比大学的床舒服。评心而论,大鸣,红缨,吴霞和我四人,我觉得睡
地上的比睡床的变化要大些,因为上大学时我和霞还满脸孩子气,到现在活了这一把年记
再有稚气岂不成了妖精。我们瞎说到四点钟还不睡,最后是说第二天的酒宴,成名酒棍吴
霞发话,“明天一定都不能喝醉,特别是彭华。”我责无旁贷得捧场,“包在我身上。”
大鸣不响,红缨却说, “放心,我绝不会喝醉。”听得我和吴霞都瞪圆了眼睛坐了起来,
真是楼外有楼,天外有天哪,得好好问问是什么级别能盛多少二锅头,一问红缨则说:
“我从来不喝酒。怎么会喝醉。”我们捧腹大笑,眼泪都笑了出来。肯定要惊动男士们,
活他们该!
五月二十五日,晴,礼拜六
一夜无眠。所谓一夜,也不过三四个小时。我一动就听得大鸣动,由此可见她也没睡。如
果说大鸣是为了明天的酒宴发愁,我又是为什么呢?每逢此时,我便感叹这世道人心不古,
真有人有福不同享,很想跳将起来大喊大叫,让有幸睡着的人们也不得好睡。分分秒秒数
到七点四十,如同被赦一样去洗澡更衣。到了楼下,见诸位男士已尽数起来,无一幸免。
这天从曹宁君驾到谈起。当年我们的小弟弟,如今成了老油条,谈笑自如,烟酒并行,五
毒俱全。不得不刮目相待。让我列一天或许前后颠倒的流水帐,看照片;照相;给于洁打
电话(这厮酷若旧日,仍和我是一对不肯说软话的搭档,为她清脆的一声“饭桶”所骂心
里就高兴);打牌(很有几个在牌桌上妙语连珠的角色,有人拉阿东下水未能成功,因为
阿东满脑袋学问装不进扑克牌了);又看照片;读大鸣书;Helen 唱歌;孙宏为弹琴 (此
帅哥好大贼胆,敢在小辈面前出洋相,或许他自恃比小子们不足比老子们太有余,瞧瞧,
明明“秋日絮语”,被虞伟说成“爱情的故事”,至于我自己旷琴四年连键都找不着了);
禹阿东指点江山,激扬科学,招兵买马;陈阳埋头读书(好似此行要大家为他大学不用功
的形象平反);去帮厨的一一被侯慧赶将出来;再照相;再看照片;最终五颜六色七荤八
素摆一桌子,坐着咽口水却不能吃,王正辉来电话了。老支居然和她众目睽睽之下卿卿我
我说了半天,还是陈阳顾及大家情绪说:“都饿着呢,都瞅着桌上的菜。”王正辉却让大
鸣传话说别急着吃。“小王,”彭华说,“我不象他们那么没出息,一听你声音我就不饿
了。”他自称不饿了,桌上不知有几个人想把他活吞了。有王正辉想着我们,也有人想着
孙立群。大学第一年,为关灯开灯彭华白坚石几乎老拳相见,据可靠消息孙宏伟说,立群
见状一字一板的说,“战争,将会为人民带来灾难。”居然玉帛止戈。一干人说就凭此话
海角天涯也得捉他出来。我赶忙找电话卡,吴霞翻出号码,一番周折从南京把他找了来。
人人拿电话就要他猜是谁,此兄猜得十分认真,可惜回回落空,大不如他那辽宁老乡王正
辉机灵。
终于吃饭有望,也得等主人彭华致词:“光阴荏苒,”吴霞和声:“荏苒啥意思?”彭:
“岁月蹉跎,”吴:“蹉跎啥意思?”彭:“二十年一聚,人生几何,何日再聚,who
knows?”举座皆乐,一致共谢被曹宁君封为生化班编外的侯慧。一巡酒鬼,二巡五粮液,
三巡剑南春,四巡二锅头,五巡洋河大曲,彭华一语惊心,“不上茅台,因为我最不喜欢
茅台。”众人附言,茅台大大地不好,徒有虚名。我想我辛辛苦苦抗一瓶茅台来进贡算是
打在马蹄子上了。彭华可恶,对我怀恨在心当众批评我,此人不知我还准备给他当保镖呢,
是男人都负心。吴霞最爱和稀泥,马上起来挽袖斟酒,风度优雅,出语更是不凡:“我敬
大家一杯,请一定干了。”果然个个见底。我来效颦,刚悠然喝了自己一杯吴霞就急了:
“你这呆子倒喝了,孙宏为陈阳都没喝,你敬的那门子酒?”“他们不喝关我什么事?!”
“笨蛋,你喝他们不喝你就白喝了。”“不是白喝谁不喝吗?”“别给我装傻,得让他们
喝,不能让他们小瞧你!”“哎呀,姑奶奶,情愿小瞧吧,我怎么让他们喝?揪领子灌下
去么?谈何容易!”我倒想开了,爱喝不喝,不喝拉倒,记上一小仇,下次斟酒偏不给你
做酒保。后来发现禹阿东,虞伟,曹宁君都是好同志,从没让我失望,斟满就见底,为此
类同志斟酒很有成就感,忍不住一斟再斟。陈阳敬酒不喝,后来却自己倒,那天喝到喋喋
不休的只有他一人。四平八稳坐在对面的支本欣,任你千杯万盏,我自巍然不动,以没有
胆为借口,抱着一瓶啤酒一滴一滴泯,岂不知吴霞和我胆里都有石头,也还胆敢当一对超
级女酒桶。大鸣红缨坐的远远的,持淑女状,手托香腮,兰花指持筷,十分有与我们俩土
匪划清界限的嫌疑,全然不顾同屋再住一回的友谊。坐另一边的胡大姐,侯慧,田洁甭说
就是淑女了。伍炯如悄悄坐在角落里,也不失为凑趣的好同志,喝的满面通红,一看就是
好人,与那帮越喝脸越白呈奸臣状的成鲜明对比。彭华早是重点保护对象,他是喝到要爬
手电筒光柱也还要嚷没醉的人,想他有些个量就让他自斟,要有谁敢撮弄他爬手电光柱,
先得把我和吴霞撂倒了再说。群丑大嚼图就形容到此,因为这种场面,我老觉得像个马戏
团,自己就是想逢场作戏又不胜任的小丑,虽有一桶之量仍然信心不足,尽管今天有另一
酒桶作靠山。席终,众人嘈杂,不知所云。
与田洁赵卫国们道了别,突然我觉得很累也很空虚,就去睡觉了。刚有睡意,一干女士们
回巢,时值大约不到两点钟,我问吴霞,要满月了,外面月色可好,她老人家答非所问,
说:“尽是蚊子。”我本家则过来揪着耳朵严历的嘱咐:“明天早上你八点以前起来,不
许洗澡!”我只有讨饶,“遵命!你放我去睡觉。”
五月二十六日,礼拜天, 晴
我醒了就头疼,酒真不是好东西,嗜酒之人智能都有问题。既然女士们不许我起来就洗澡,
我就得冒险下楼了。天还没怎么亮,希望男士们不要睡得象枪战过后尸横客厅,那样的话
我就得到后院去喂蚊子了。比我想象的要好,男士们居然全起来了,想必比我还睡的少,
很让我长了几分同情心。突然见田洁尚在,赶忙拍拍脑袋看是不是还在做梦,原来田洁是
来为女儿找书,可怜天下父母心也。书为不知哪位绅士从沙发里翻了出来,田洁就此道别。
一早上似乎无所事事,想必是酒没醒记不清。唯一记得的是与支本欣作倾心之谈,谈的除
了我们家邻居Peter Wipf是与老支有机合成的同行,再就是小型土木工程,怎样用混凝土,
或花砖改side walk 或driveway,诸如此类。我感到受益匪浅的是老支的平和稳重,简直
是醒酒汤,任何酒鬼与此君一席谈便无发酒疯的可能。正在此时有我的电话,很让我诧异,
难道彭华把我行踪告诉了梦鸿珩瑛?一听居然是楼上几位同“寝室”的高士,上了楼就挨
一顿训斥,说大清早连影儿都没了,上哪儿跟谁私奔了,这都哪是哪儿啊?早起洗澡不许,
悄悄溜出去也不好,这些个不省油的灯,真难伺候!想当年还说过此类蠢话,如果大鸣是
男人,我定要赖着嫁她,如果我是男人,我定要娶吴霞(还是于洁?或俩兼之?),谢天
谢地没曾娶嫁这一干人。
早茶吃的什么就都猪八戒吃人参果了。说的什么还有印象。孙宏伟大讲恋母情结,除了他
自己还举出一系列有此癖的志同道合之士,似乎不恋母就不是好孩子,我都想宣称“我也
恋母”,至少滕秋克和我妈都是自然卷发,没等有机会大鸣有电话,打开手机就一脸慈祥,
“妈妈在干什么呀?妈妈在吃饭。”我猜是她那个比我儿子小一天的小家伙打来的,轮到
我就得我追着我家俩小祖宗问好了,他们一点儿不恋母,比孙宏伟差远了,好让我痛心疾
首。席间彭华声讨他一熟人,说好好儿就吃起斋念起佛了,连鸡蛋都不能吃。如果说老支
的平和稳重对我如同醒酒汤的话,彭华的激进对我如同战斗的号角,我一下就做好了争论
的准备,比如“美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差异”,“有人能为信仰而
克制己念是他荣幸”,但我刚问出个“这有什么不好”就被吴霞在桌下踢了一脚,又加上
些“奶酪油多不多”的废话来打叉,遇到这种吃里爬外拉偏架的朋友真痛苦,连帮了半截
子忙的陈阳都打了退堂鼓,我只好伸伸脖子把话和整棵芥蓝一起咽下。话没说痛快见阿东
去争付款,很希望他们能大打出手,结果没打起来,扫兴。去书店很消磨了些时间,没见
什么想读的书,买了几盘VCD,也是对我家小祖宗“你不想我我还惦记你不跟你一般见识”
的一点表示。
回到彭华家,第一件事就是为三室友不轨之密谋,将吴霞数字相机里的照片尽数删去,尽
数是不慎也不幸的结果,因为把那些千载难逢的集体照也牺牲了,只得又照了些行李箱铺
盖卷之类来滥竽充数,此番让我也恶作剧一下。好景不长,怨不得我这人没出息,很快我
就觉得君对我不仁我不能不义,还是当面说清。果然吴霞大惊小怪,把无辜群众都拉出去
再用她相机重拍一番倩影。
昨天彭华一挥手就分派孙宏为带我去机场。行期将近,我收拾好行李换了衣服,心乱如麻,
好像有很多要说的话没能够说,细想真还不知道要说什么。这时候妍妍开始弹琴,弹得那
么好的圣桑第二交响乐对我算是对牛了,怨不得古人要到清风明月的去处操琴弄筝。大鸣
拉着我说,“不能送你了,因为有去无回。”如此精辟之言说得我心酸,我们可不都是有
去无回吗,大学一毕业可不就有去无回了嘛。在彭华家门口,我昏头昏脑一一握手,心里
唯一的念头就是好好儿数着,一定得个个握到,绝不能少握一个。这时彭华说出个“第二
次握手”,恨得我牙痒,这样的关键时刻怎能提数字呢?漏了一双手没握算谁的责任?罢
了罢了,贾宝玉出家时连宝姐姐袭人姐姐都顾不得了,你们这些家伙这么多年没见几个不
也活了下来。去也去也,终有一别。
从机场来时我是与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吴霞同行,去彭华家的路她烂熟于心中;去时则跟随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孙宏为,怎么去机场对我对他都是未知。上了59号我就看到机场方向的
狰狞阴云,我说要下雨孙宏为说不会,我给他地图他说不用。过了一会儿果真电闪雷鸣,
瓢泼大雨里宏为很开的潇洒(大约有人好奇我是否当面对宏为提过time machine, 实情相
告,岂敢!怕为这高深莫测的仁兄把我扭送到精神病院), 可是一下高速,我们就走错了
路。宏为发恨说真不信我会迷路。好让我感叹,方向感好的人迷了路会这样锤胸顿足,象
我这样自封的迷路大王走对了会喜出望外。在波士顿住的几周买菜就没能有几次直奔家门
回来。最惨的一次还是在你们华盛顿DC,从Shady Grove Metro Station 出来,一辆
minivan 后面装满七嘴八舌的小崽子,多说了几句话就不知哪儿去了,那天既没地图又没
手机, 天阴下雨没东没西,住宅区里连问路的鬼也没有。见一群人漆房子,大喜,谁知一
问都是老墨,会的英文不比我会的西班牙语多,如有人远看我们谈话一准儿以为我们在做
广播体操,有一黑瘦小子听懂了highway 两眼放光,立马跳出来长青指路,他一指就把我
指到28号west上,如果我犯迷糊多踩几脚油门,开过Potomac River 就去Virginia了。这
Houston 一马平川,不过多走几条街, 有何难哉。果然,没半里地就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到了terminal,孙宏为的方向感又不灵光了。他问:“你能跟我一起下车吗?”我说:
“为何不能?从你的terminal可以坐地铁去我的terminal。”“地铁在哪儿?”“地铁在
地下。”“你怎么知道?”“我从这儿来的我怎么不知道?!”“我从这儿来我怎么不知
道?!”“难道你不知道的我就得不知道?!”尽管来路上为了何去何从我们小有异议,
但最终我们都到了各自要去的去处。
告别了孙宏为,离我飞机起飞还有近一个小时,看着晴天白云下繁忙的空港,飞机有起有
落,想起长春火车站,生出几分感叹。多谢各位,我们能有今天的聚会,特别是当年的班
长彭华,靠他的凝聚力把曾口出狂言“没谁想见”和诉苦连天“要开会”“要搬家”“老
公要出差”的都召集了来,更有压寨夫人侯慧,如此热情款待我们九流三教乌合之众,这
短短的两天,对我将是不能忘记的日子。为此我感激你们!离开长春后,特别是在吴霞来
美之前,我几乎忘了自己曾是吉大人。如果没有吴霞,我就会是我们班断了线的风筝。二
十多年的友谊,直接的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从哪里来,间接的引导着我向何处去。我们曾有
五年的缘分,那是我们刚刚踏入人生的五年,是我们青春的五年,是决定我们是谁的五年。
那时我们颇有象乌眼鸡的时候,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如今我真还想再乌眼鸡一次,
可惜暴雨雷鸣电闪也没把宏为开的车变成time machine。我们只有向前走,别忘了向两边
看,最终会融化在蓝天里面。
2002年8月
后记:
最近我重看了Woody Allen的77年Oscar获最佳影片奖的Annie Hall, 87年一老美推荐给我,
我那时看了很喜欢但对其中的jokes 不尽理解,不是语言而是年龄问题。若无这次聚会我
还不能理解这么透彻,故附在此与各位共享。
他开场的joke:
俩老太去吃东西,一个说难吃,另一个说不仅难吃,还给那么少!他说这就像生活(life),
有那么多的孤寂,苦闷和些许的快乐,却如子在川上所曰,逝者如斯夫。结尾时他已与
Annie 分手,讲了另一个joke作为结束语:一人见心理医生,说他兄弟疯了,认为自己是
鸡,心理医生说你带他来,他说,不行,我还想要鸡蛋呢。Woody Allen 说这如同rela-
tionship (love),明知有那些个疯狂,呆傻,痛苦,不明智没逻辑,还有人惦记着那可
望而不可及的蛋。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life is about love,广义与狭义的love,短暂和长久的love,铭
心与肤浅的love,具体和抽象的love,自我和宏博的love,最起码是对食品的love。让我
们用我们各自的方式热爱人生吧,尽管它为我们带来太少的快乐太多的折磨,二十年不过
一瞬间。就是它对我不仁我又怎能对它不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