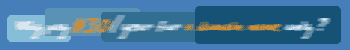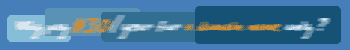一晃,快是十年前的事了。
初夏的一天,美国朋友家Brad邀请我到他家作客。到了他家后,他母亲拿出
了一碟她自己做的点心请我边吃边谈。小点心很好看,五颜六色的,有许多
不同的形状。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美国人家中吃美国人自己亲身作的美式
点心。为了这个第一,我毫不犹豫地就拿起了一块,吃。可我刚咬了一小口,
心中就直叫苦,啊!太甜了!甜死人了。
Brad看我那么痛快地拿起来就吃,就我问味道如何。那时我还不理解美国人
的习惯,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怕扫了主人的兴,就微笑着说,很好。他
见我如此赏脸,就请我尝尝另外的一种,我无奈了,只得硬着头皮又吃了一
块,甜得我连连叫苦不迭。
以后跟人开玩笑,说从前留洋回来的人讲,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事就算
是真的,咱也不敢讲,免得戴上一顶“崇洋媚外”的帽子,太重,这头担当
不起。但这美国的饼乾真的是比中国甜,甜得我牙都要倒了。小时候听老人
说,以前谁家的媳妇要是把菜作咸了,婆婆就会挖苦说,怎么,卖盐的不要
钱了!这话要是拿到美国,就得这么说了:怎么啦,这卖糖的都不要钱了!
回答一定是,是啊,是不要钱了。当然,钱还是要的,但美国的糖实在太便
宜了,跟不要也没有什么大区别。不到两美元,就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五镑
白糖。我的美国老师听说我买了两镑糖居然使用了半年多,简直无法相信。
她告诉我,她一个月就得用四、五镑白糖,这,我也无法相信。只是后来和
美国人打交道久了,才不得不信。
我怕美国的饼乾和小甜点,不吃也就罢了,问题是太多了,我就是不买,也
有人送上门来。
我有两个孩子,小的上幼儿园,老大上小学三年。隔三差五的,他们就会从
学校中带来一些甜点,也是五颜六色的,也是什么形状的都有,有的是老师
给的,有的是学生家长给的。就连个情人节,小小的孩子,才八岁,学校中
也庆祝一番,且有一个礼拜之久。前一天儿子从书包中能掏出一把饼乾,后
一天能掏出糖果。也许是从小我就很少给孩子们吃甜点的原因,他们也不喜
欢这么甜的饼乾。
问题是他们洒脱,不喜欢就不吃,随手就扔了,一点也没有内疚的感觉。而
我就难了,吃也不是,扔也不是,到头来,还是得吃,硬着头皮吃下去。多
年的习惯了,改不了,不能糟蹋粮食。从小老人就教导我的,饭要吃乾净,
不能扔掉。我想当年母亲教导我不能糟蹋粮食时,她指的肯定仅仅是饭碗中
的饭:如玉米粥,高粱米乾饭,绝对不会包括糕点。那时只有在过年过节时
才能吃上一两块饼乾,爱都爱不过来,怎么可能糟蹋?也不包括大米饭和白
面馒头,那也是很少见的,还限量吃,怎么可能糟蹋?其实母亲根本就不必
教育我们,那么多年,我们家的粮食一直不够吃,我们就是喝玉米粥,也都
把饭碗舔得乾乾净净的。
七、八年前,我在我们的社区大学CLC上写作课时,写了一篇我童年时代挨
饿的故事。美国同学问,你们家怎么不把剩饭放到冰箱里呢?我告诉他,那
时,我还没有听说过冰箱这个词,再说了,也从来没有剩饭。我们之间无法
沟通。
就在我写那个故事的那几天,我一边写一边流泪,哭得心都疼了。我又回忆
起了我一生中最凄惨的一幕。那年大概是六一年,我六岁,正处在所谓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自然灾害”,说白了,就是“大饥荒”,全
国上下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万幸,没被饿死,但饿晕了,一天到晚脑袋
里转转的只有一个字:“饿”,或者“饿死了!”
全家人都在挨饿。母亲天天饿着肚子到生产队干活,姐姐和哥哥则饿着肚子
上学,家中只剩下我和弟弟,饿着肚子玩。那时,我们家吃饭已经限量了,
晚上那顿饭,一人就一碗稀粥,有时是玉米粥,有时是高梁米粥。粥稀得已
经不能再稀了,饭碗中有多少颗高梁米粒,都能查出来。母亲把饭放到我眼
前时,我赶紧就端起来,先是贪婪地闻一下,然后猛地就喝一大口,这一口
就能下去一半的稀饭,然后把饭碗沿着右边转半圈,再向左转半圈,不出四、
五个半圈,一碗稀饭就喝得底朝天了。然后,用舌头把残留在碗边和碗底的
稀饭舔得乾乾净净。吃完了,就把下巴支在手上,看哥哥和姐姐,看母亲。
母亲总是最后为自己盛饭,盛好了也不吃,看着我们弟兄一个个把饭全吃光
了,她就把她饭碗里的那点,给孩子们一人分一点。她自己常常什么也不吃。
母亲是最先浮肿的。在她的腿上一摁,就能摁出个小小的坑,半天平不了,
我还觉得挺好玩的,就在母亲的腿上摁了一下又一下。母亲就是那样,但还
得去生产队里干活,挣点买粮食的钱养家糊口。
养家糊口,这四个字太准确了。母亲去干活了,就留我在家照料弟弟。弟弟
才三岁多,而我也就大他三岁,也还是个孩子。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每天
是怎么照料弟弟的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曾经照料过他。但穷人家的孩子好
养活,干活干得早,母亲也就放心让我看弟弟了。何况,她就是放心不下,
也得放,没办法,活命要紧。我也没有把自己照料弟弟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
妈妈每天叮嘱我,多加点小心,离火远点,别把弟弟烫着了。别让他满地跑,
摔着了。哭两声没什么。我点头,知道了,也就那么做了。
最难为我的是妈妈还让我为弟弟作饭,作好了喂他吃,或者看着他吃下去。
这个诱惑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大了。稀饭一煮好了,那股香气直冲我鼻孔扑来,
怎么闻怎么香。当时也真不明白自己的鼻子为什么那么灵,一点点香气都能
闻到心里。还不明白的一件事是:肚皮明明已经饿得憋憋的了,怎么一喝口
水,里面就咕咕地响。
家里烧的是和着黄泥的煤,母亲干活前,在炉子当中扎了一个眼,到那个眼
中的火变红了,就是我给弟弟作玉米面粥的时间了。半碗水,一小饭勺面,
就是弟弟一顿饭的定量。我先用一个大姐用过的小旧锅烧上一碗水,又在另
一个小饭碗中,加点凉水,把那一小饭勺的玉米面搅和匀了,看着小旧锅里
的水翻个了,就把和好的玉米面放到锅子中,然后赶紧搅和,别糊锅底了。
当粥快好了的时候,我会像作贼似的偷偷尝一小口,从来不敢多尝,怕弟弟
饿了就会哭个没完没了,怕弟弟等母亲回来时告我的状。
饭作好了,弟弟也等不及了,他几口就把一饭稀稀的玉米面粥吃光了。看他
吃完了,我就把他饭碗中剩下的一点点东西都舔乾净,然后把锅里的再舔乾
净。有时,把锅舔乾净了,还不放心,再加点水,使劲晃晃,把这点水喝到
肚子里。
有一次,弟弟不舒服了,也许是感冒,或者肚子疼,妈妈就给他买了一小包
饼乾。那种小饼乾一个个只有小拇指指甲那么大,圆乎乎的,带着奶黄色,
我们都叫它“奶豆”。在我那双饥饿的眼睛中,这些奶豆比金豆还贵重、还
稀罕,因为我已经几乎忘记饼乾是什么味道了。
妈妈走前嘱咐我,弟弟要是闹的时候,就给他一、两个吃。不久,哥哥也上
学走了。只有我和弟弟待在家中。 弟弟也早就盯上“奶豆”了。不一会儿,
他就闹了。
这时,“奶豆”充满了我的心灵,吓得我连放在碗架上的那个饼乾包都不敢
多看了。弟弟闹着要吃奶豆。我胆颤心惊地打开了纸包,数出了几个奶豆,
一个个地递到了弟弟的手中。看着弟弟吃下了一个又一个奶豆,看着他那满
脸的幸福,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央求弟弟给我一个吃,央求他不要告诉妈妈,
我就只吃一个。弟弟终于答应了,他给了我一个奶豆,我急忙把它塞进了嘴
里,嚼两、三口就吞下了。是什么味道,不知道。
我馋疯了。
我不知怎么了,吃完了一个奶豆后,就把又一个奶豆也塞进了嘴里。弟弟大
哭起来,我自己也楞住了。就在这时,我听到门“咚”地一声被推开了,两
个哥哥冲了进来,我以为他们已经去了学校,哪里知道他们竟然藏在门外,
等待抓我这个贼。他们一冲到我面前,就一人打了我 一个大耳光子。
我吓坏了,疼死了,就大声地哭了。
哥哥们大声地喊:不许哭!你抢弟弟的东西吃,还有脸哭!
我吓得又赶紧闭上了嘴。
他们又严厉地教训了我几句,讲些什么,我现在一点也记不清楚了。记得自
己就那么傻乎乎地站在地上听着,一声也不敢吭吭。脸上火辣辣地疼,更疼
的是心里,我真是丢尽了脸,丢尽了人!
哥哥们终于上学走了。
一听到关门的声音后,我就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痛哭。是委屈、是怨恨、还
是悲哀,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想哭。三十多年后,当我回想起这一段往事时,
我依然禁不住还泪流满面。
那次,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连奶豆都吃不到,我不想活了。
三十年后我来到了美国,到了华人教会,许多基督徒向我传福音,告诉我神
爱世人。但我听不进去,我的心中有太多的苦毒、太深的苦水。我经常想到
的就是我为了偷吃两个奶豆而想到了死这一件事。我不明白,一个像我那样
的小孩子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竟然在将近三年多的时间中经常被饿得死
去活来。当我为了能吃上一口饭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还有那些被活活饿死了的老百姓呢?当那些被纳粹赶进煤气炉中的少年少女
在挣扎时,当那些被日本兵挑在刺刀尖上的婴孩尖叫时,上帝在哪里呢?
我想了三年多,还是不明白。
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我们是在自食苦果,并且,我们用自己的罪孽来不断
地培养这苦果,使之不尽不休。青少年时代我真的相信“三年自然灾害”是
由天灾造成的。那年雨下得真大,不仅我们的院子里积满了水,就连屋子里
都进了水,水有时都会满了炉坑。但文革后报纸上陆续告诉了人们一些真相,
说早在一九六二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尖锐地指出,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原因,
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但那“人祸”是什么呢?上面的统一口径是
“左倾”,说是背离了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瞎指挥,等等。
说得太轻巧了。那是几千万饿死的冤魂哪。我现在也不想从政治与制度方面
去解剖根源了,一些人已经那样作了。我看到的是人性的根源,是灵性的根
源。“人祸”之所以是人祸,“人祸”之所以构成了人祸,就在于人要冒充
上帝。而这个人,无论他以什么面目出现,是一个领袖,还是一个集体。他
或者他们和我一模一样,都是一个罪人,心灵深处都潜藏着一堆可怕的魔鬼。
但魔鬼若不是就在人心中,它怎么可能出现在人的生活里?若不是社会给予
了合法的条件,那邪恶怎么能大行其道?
很小时我就会背诵一首民歌,出自郭沫若和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天上
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齐开道,
我来了!人以上帝自居,这就是一切人祸的总根源。 人心中最可怕的恶魔,
常常并不是露出了一副青面獠牙,张牙舞爪的形象,而是打扮成得无比美丽
的天使。他许诺给人一个人间的天堂,并要领着人们向它直奔而去,但有一
个条件:就是人们都必须无条件地听他的话。这必然要造成人祸,不论那上
帝的扮演者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还是邪恶的念头,他都注定要把人引导到地
狱中去。人祸,就是由人悖逆上帝的罪孽所酿下的苦酒。
但面对着人间悲剧,我没有省察人的罪孽,却埋怨上帝不公、不仁,这岂不
是为人与制度的邪恶开脱罪责吗?
并且,不止是他,还有我,不止是他们,还有我们。难道我们就没有亲身参
入多年来发生的一次次人祸吗?我怎么能说不呢?正是由于我们参入到了那
人祸之中,并且,是将整个身心都全部投入,所以,那人祸才能那么残酷、
那么广泛、那么持久。
令我自己感到更可耻的是:我在责备上帝的同时,却没有把自己在生命中享
受到的一切归于上帝的恩典。我赤条条来到了这个世界,没有带来一缕阳光,
一丝清风,一滴甘露,这一切,都是赐给我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向赐给我这
一切的上帝道一声感恩。
虽然我明白了这些,但我还是不明白,当无辜的小孩子在受难时,上帝在哪
里?
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他在十字架上。他与我们一同经历苦难。
经上说,当耶稣看到拉撒路死了,他哭了。
经上说,当耶稣被钉在嘴两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
“耶稣哭了。”
“我渴了。”
这两句话像母亲的双手一样温柔,它抚摸了我心中那深深的伤痛。它使我明
白了:虽然上帝没有拿去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虽然上帝也没有对我
清楚地解释这一切苦难为何发生在我身上,但他,创造天地的主,和我一起
经历着我遭遇的苦难。 这,就足够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