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一辈子活得真难
在那些心里焦急的日子,我想起了父亲的这一生.父亲这一辈子活得真难。
自从父亲年轻时闯关东后,尽管到老了,他还是满口的山东话.他多年来反复告诉我们兄弟姐妹,咱们的老家是山东诸城大黄滩.七十年代末,父亲离开老家已经快四十年了,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逐渐开始好转了,父亲就老是惦记着回趟老家,他经常唠叨说,我得回去看看了,到你爷爷奶奶的坟前磕个头,薅两把坟上的草。
可是,一开始是姐姐,后来是哥哥和弟弟的孩子,一个个都要靠母亲和父亲亲手来带, ,父亲怕把孩子都扔下给他的老伴,把老伴累坏了,就想等这些孙男孙女大一点再说,等到他们都大了,上小学了,父亲刚庆幸自己终于可以挪开手脚了,偏不巧,母亲病重了,一点离不开他,就连父亲去丹东两天,母亲也叫哥哥催我父亲快回来。
父亲回老家的心愿落空了。
自从我上了中学以后我就认为,父亲没有大志。从我懂事起就一再听到他对我们弟兄姐妹说:孩子啊,要是你们长大后能出息个人,有碗粥喝,我就是腿一蹬,走了,也放心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说的总是有碗粥,他从来就没说过有碗大米饭。
只是当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父亲的心酸。
在被上面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那几年,我们兄弟姐妹常常饿得死去活来,晚饭时大都喝稀粥,不是玉米面稀粥,就是高粱米稀粥,并且严格限量:一人一碗。那稀粥稀得能照出人影来,一点也不抗饿,半夜饿得老是睡不实.
晚上肚子里的东西消化得慢,还好熬,白天就更难熬了,只好跟着哥哥像野狗一样到处找能咽下肚子里的东西吃.什么野菜,树叶,得着什么就往嘴里塞什么.后来树叶子撸光了,哥哥就带我扒榆树皮吃,搁到嘴里嚼嚼,还挺滑溜的,我就使劲地吃,直到撑得再也吃不下去.
一连好几天胀肚,去一趟茅房,拉不出屎来,再去一趟,还是拉不出屎,一蹲就是半个来小时。到了第四天也许是第五天,我蹲在茅房里,憋得出了一头冷汗,疼得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大哭,喊:妈!妈!被邻居听到了,有的就叫我憋口气,再使点劲,有的就跑到一两路外的生产队的菜地,把正在地里干活的母亲喊回来了.
母亲一看我疼的那样,就从家里一斤装的豆油瓶子里,倒出了一羹匙豆油,接着又一羹匙,喂我喝下去,过了一阵子,看还是不起作用,母亲就用一根小细棍,一点一点从我的肛门里往外抠硬成了一团的大便,一边轻轻地抠,一边轻轻地问我疼不疼.
记不得母亲哭没哭了.只记得她说:妈这是哪辈子作的孽呵,你怎么摊上了这么一个没能耐的妈呢?
母亲说的话是把父亲也包括在内的.
按理说父亲不能算是没有能耐的人.
当时父亲在食堂工作,是炊事班的班长.在他那个大食堂里吃饭的,有好几百个建筑工人,他要是顺便往家中带点吃的,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误。父亲每一次探家回来,我们也都盼望他能从那个旧包包中掏出个馒头,或者窝窝头来,但父亲每次都是空着手回来的.
有一年他们建筑公司在离我们家十多里的地方施工,我大哥就走着去看父亲,到了工人吃午饭的时候,虽然父亲最心疼自己的大儿子,但他还是叫我大哥回家,怕影响不好。(因为炊事员是随便吃,没有饭票.)一起工作的工友实在看不下眼了,悄悄地往我大哥的口袋里塞了两个馒头,把我大哥领出了食堂。
父亲常对我们说:作人得有骨气,你就是饿死穷死,也不能作贼,不能低三下四地求人、巴结人。
父亲的确不会巴结人.多年后听父亲的老工友说,你爸这个人是死心眼.他在食堂当炊事班长那么多年,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从来不知道偷偷送点大米白面给厂长和书记.有一次某书记买菜时,有个炊事员给盛了满满一大勺子,你爸一看就火了,叫他重新盛,还当着人家书记的面,说你小子真会拍马屁.
他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故事,说有个炊事员给工人盛菜时老是给的少,有一次叫你爸逮个正着,那小子盛了一勺后正在往下晃,你爸就说他,你那个胳膊穷哆嗦什么啊.你说你爸爸这样能不得罪人嘛.
父亲的确得罪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关进了学习班,要交待贪污的问题!整他的积极分子说:你老范头要是不贪污,你那一大堆孩子是怎么养活大的?!
父亲也急了:说你们要是能查出我范锡章往家拿一粒米,你们就把我拉出去毙了.
建筑公司的人到我们家所在的居民组调查了几次,没发现问题,我父亲就被解放了.
父亲从成为国家正式工人到退休,将近二十年的工资一直是每月不到四十六元钱。他除了留下几块钱交饭伙外,剩下的都交给了母亲。其实,不仅是整我父亲的人不明白,就是我直到今天也还不明白,母亲怎么能用四十来块钱把我们家这一大堆孩子拉扯大呢,并且,在文革前,两个姐姐就上了大学?
但有一件事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那就是越接近月末的时候,母亲的眉头就皱得越紧了。
在那二十年间,父亲只和我们一起过了一次春节,我青少年时曾为此而兴高彩烈。后来才知道了,父亲之所以不回家过年,就是想多挣个三元、五元的加班费。
爸爸,大年三十了,大年初一了,别人都回家过年了,到处都能听到爆竹声和拜年声,但你却一个人坐在冷冷清清的食堂中。爸爸,你想了什么呢?爸爸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当我今天真想知道时,你已经不在了。
一转眼,有十多年没有回国与全家人一起过年了,过年时想家的那个滋味,我尝了整整十年。但我还是无法想象父亲因贫穷和无助而无法回家过年的心情。我唯望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原谅他儿子当年的无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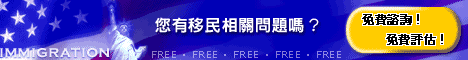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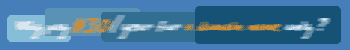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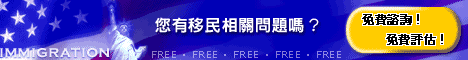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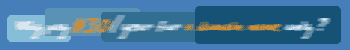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