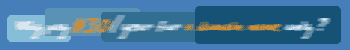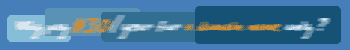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对不住美国。别的不说,就说这住,来到美国快十年了,一直
居住在芝加哥的北郊,算起来,活了这么多年,除了故乡外,芝加哥北郊是我居住
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了,怎么也算得上是第二个故乡了,但我总觉得这是他乡。自
然了,美国是永远的异国。
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呢?除了这张生而有之的中华脸之外,语言当
然是首要的原因:英语是外语。
许多来美探亲的老人,对美国的最大不满就是,他们(美国人)怎么都讲英语!好
端端的一个中国人,任你过去如何才华横溢,口伶齿利,可一到了美国,就哑了、
聋了。如果你不会开车,还要加上瘸了,没有腿了。我虽然没有堕入如此的悲惨世
界,但也一直在边上转悠着。虽然会点英语,但只是点而已,这辈子也指望不上像
汉语说得那么溜道和地道了。至于听,也好不到哪里去。而写,就是梦了。由于英
语不是自己的母语,所以,美国人的英语讲得再标准,我听起来也不如家乡话那么
亲、那么有味。什么味道呢?说不明白,但能感觉到:就是心里头顺道,浑身上上
下下里里外外都舒坦。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邻居。故乡不能没有父老乡亲,不能没有邻里。少了乡亲,
没了邻里,就是乡土也将失去迷人的味道。但在美国,我没有邻里乡亲。这当然不
是指地理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说乾脆了,是感情意义上的。我们
家也有邻居,相邻而居的,左边一家,右边一家,对面还有两家。可我搬到新家已
经两年了,和屋子对面的邻居家的男主人只打过两、三次招呼,还都是在冬天下大
雪的时候,我们都从各自的家门开始,扫门前雪,扫到路边了,隔着车道,彼此微
笑着打个招呼:“哈喽!”或者更简单:“嗨!”,房南边那家的男主人,是一次
割草时幸会的,他快步走过来,对我说,地界在这里,这地方的草应当你们自己割。
说完就走了。倒是北侧的邻居最友善,我们才搬来三天,女主人就送来了一盘点心,
平时也说点什么。
和我交往最深,应当算北侧邻居家的狗。许多美国人把狗都当成了家人,还给它们
起了个正经的名字,我们邻居家的那个狗就有名,叫高尔特(Galt)。我和它熟悉
了后,见到它常大声喊:“Galt!”它就知道我是喊它。说来惭愧,我不善于记人
名,中文都不行,英文就更不行了。所以,除了北邻的男主人外,其他邻居的姓氏
大名,我是一概不知的。我能记住“Galt”的原因,除了它可爱外,是因为我老喊
它,而且,一喊它,它就摇尾巴。我相信它那么作,的确是出于高兴,而不是出于
礼貌与客气。因为,有时我在门前走忘记喊它了,它就叫几声,直到我注意到它为
止。慢慢地我听明白了,那汪汪高叫,也是以求友声的。
看到Galt它对我那么友好,我有时就忍不住走到邻家的院子里,而Galt一看我来了,
就更加亲切友好了,它扑我舔我,撒完欢后,往地上一躺,等我给他挠痒痒。去年
我回大陆探亲回来,Galt是第一个用狗声表达了对我的热烈欢迎和深切怀念,而且
持续了好几分钟。它的女主人忙推开门,看发生了什么事,发现是我回来了,笑了,
“嗨!”
老子向往着一个虚幻的远古时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在最发达的美
国社会中已经成为现实了。当然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就是犬之声依旧,而一唱雄鸡,
却难得一闻了。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想到“邻居”这个词,并且,常常把它同沉默联系到了
一起。如果你的邻居是沉默的,或者,你对你的邻居保持着沉默,老死不相往来,
那么,虽然是比邻,其实与天涯也差不多一样远了。就自己的居住来说,王勃的那
句名诗也许可以篡改一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如今应当改为:“海
外无知己,比邻若天涯”。
出于好奇,我想明白邻居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于是,就翻开了手边的〈辞海〉
和〈辞源〉,原来,我们的祖宗是这样解释邻居的:“睦乃四邻”,“邻,犹亲也”。
说得好!它正抓住了我盼望的那种状态和感情。
看罢词典,我站到窗前,漫无目的地看着小街对面的邻居家,四周连一个走动的人
也没有。就这么看着看着,我不知怎么地了,有点想念故乡了。我想起了自己从小
长大的那个大杂院─“刘家大院”,想起了在那个大院子里居住的十二、三户人家。
从我记事起,大家就一直住在那里。还有和我年龄不差上下的那三个女孩子,我们
从小就在一起玩,又一同上小学,上中学,不论小学还是中学,我们都在同一个班
上。
但我想的最多的却是另外一个人,也是老邻居,只是她是一个老太太。她家在“刘
家大院”旁边,叫“吴家大院”,但不像我们“刘家大院”这么大,也没有个院子
的规模。但离我们家最近,只隔了一条窄窄的泥土小路,不到十米。
在我的印象中,这位老太太一直是沉默的,我几乎从来没听见她与谁说过什么话,
更不必说大声地说话。我也没看见谁和她站在院子里聊过磕,或者她主动同谁打过
招呼,至少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打过招呼。她见到了人,总是赶快就低下了头,规
规矩矩的,连脚步也慢下来了,似乎连气都不敢喘得粗一点。
看了她十五、六年中,我从来没在她的脸上看见过笑容,连微笑也没有。老太太的
脸黑黑的,挤满了重重叠叠的皱纹,一道比一道深。她的眼神该用什么词汇来描写
呢?阴沉,阴郁,还是麻木?我不知道。小时候我想到的词是“阴险”,现在看来
肯定是错了。但那是什么样的眼神呢?我就是到今天也说不明白。当年只是感觉到
了,她的眼神好暗淡,好冷,好像是坟墓。
老太太个子矮小,一米五左右。人瘦瘦的,还加上了两只小脚。走起路来只能是小
碎步,一个劲地向前挪,风大了,就能把她吹跑了。一年到头,她穿的那一身衣服,
除了黑色的,就是灰色的。也许,那就是她命运的象征:一种无言的黑暗。
一种无言的黑暗笼罩着老人的大半生,或者说,她真实的人生,就像是一个黑色的
影子。在所谓光明的新社会中,她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岂止是多余的,简直就是
可恶的、可弃的,是毒瘤,是毒蛇,是魔鬼,必须全部消灭,并且越快越彻底越好。
她是“地主婆”。
我们都叫她“地主婆”。
“地主婆”不是人,而是“坏人”、“敌人”、“坏分子”。
自从土改(“土地改革”的简称)后,老太太的丈夫就被划为“地主分子”,属于
“人民公敌”。而她自然就是地主婆了,也是“人民”的“公敌”。至于她叫什么
名字,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大概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丈夫姓吴,但我从来就没
听到街坊邻居有谁管她叫过吴奶奶、或者吴大娘、吴大婶、吴大嫂。至于太太一语,
早已经被革命革掉了,自然更不会有人也绝对没有人敢称她为吴太太。也许很久很
久以前有过,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肯定没有我,没有我哥哥,也没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
自从我知道我家对面住着这么一个人(我那时认为她根本就不配成为我们家的邻居,
不过是住在那的),自从我知道她是“坏人”(地主和地主婆都是坏人,这是从小
就刻在我心里的革命真理),我和朋友们就都叫她“那个地主婆”,或者“那个老
地主婆”,更简单的就是三个字:“地主婆。”
我们那个胡同的五、六十户人家中,就只有她是地主婆,而且这个地主婆的政治帽
子,她从土改那年以后就一直戴着,由于东北土改改的早,所以,她比关内特别是
江南的地主们,早戴了至少两年以上的政治帽子。但等到地主们、富农们都被带上
帽子了,就一样了。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了,他们都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对象。
我看到了一次老太太被斗的大会,是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农民的斗争简单有力,不
念什么批判稿,要骂,而国骂的那三个字是少不了的,连妇女也如此骂。骂完了问
你老实不老实,回答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接下来一定要打,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吴老太太不抗打,社员们一推推搡搡的,再加上打嘴巴子的,扫荡腿的,几下子就
把她打倒了。当时的革命口号就是:我们一定要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
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老太太是没有翻身。一直到我二十多岁那年,离开故乡到外地求学,她虽然已经垂
垂老矣,但还是一个没有被“摘帽”的地主婆。在她临死前,她是否被摘下了“地
主婆”的政治帽子呢?我不知道。其实,她到底是哪一天离开了人间,我也是不知
道的。
我现在所能知道的就是:在她活着的那个下半辈子中,老人没有被她的邻居们当成
一个人。不,她甚至没有被她的邻居们当成一个会说话的动物。除了在批判斗争她
的大会和小会上向她吼着、叫着、跳着,或者举起、抡起拳头要她低头认罪、老老
实实交待问题之外,她的邻居们对她一直保持了沉默。
而我,就是那些沉默的邻居中的一员。
我从来没有与她说过一句话。
在那二十多年中,我常常见到她,但我从来没有用看人的目光瞧过她一眼,从我的
眼睛中发出的目光,是仇恨,是厌恶,是鄙视。更多的时候,我甚至连瞧她一眼都
不肯。见到了她,脖子一扭,就把头转过去了;或者,快走几步,就像躲避瘟疫一
样。二十来年的老邻居了,并且,年龄上又是我的长辈,可我不但没有和她说过一
句话,就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过。
而我、我们家,和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私仇。
我表露出来的是公恨,从我的目光,到我的无语。
一个少年的冷漠目光,和他的沉默无语,足以使一个老人的心寒透。
也许,老人在死前,早就忘记了曾经有过我这么一个小邻居,我相信事实肯定是这
样的。老人如果记得我,我相信她甚至会觉得我比其他的小孩子要好,因为我没有
当面骂她,没有朝她脸上吐吐沫,没有往她家的窗户上扔石头。但无论老人记得还
是忘记我,我却忘不了我自己,我忘记不了我的冷酷和无情,我忘不了我心中的仇
恨,我忘不了我那鄙视她的目光恰是是一把把尖刀,刺向的正是她的心脏!
其实,有那么多的机会,我是可以对她说点什么的,或者就是打一句招呼,哪怕不
称呼她什么,就带着微笑问一句“吃饭了吗?”我相信,假如我问侯她了,她就是
到闭上了眼睛的那一天也忘记不了的。但我却沉默了,但我却把头扭过去了。
现在想起来,我无论如何都是应当和她说点什么的。
因为她的儿媳妇是我小学时候的老师,对我很好。我一见到她的面,就尊敬地喊
“毕老师”,或者“毕老师好”。虽然文革一到,毕老师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但
老太太的孙子毕老师的儿子还是我多年的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班上,但一直都在一
个年级。
是的,我无论如何都是应当和她说点什么的。我上中学时,上学和放学,时常和几
个同学一起,说说笑笑地从她家的门口路过。但是,只要她一露面,我们就一下子
什么也说、也不笑了,一个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面孔,顿时成了冷面。冷面
的哑巴。
记不得哪一个什么家说过了: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但记住了有一句话是鲁迅说的,
大意是: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眼珠都不去转它一转。
当一颗仇恨的心对他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在心里是没有把那个人当成人看待的。
事实就是这样,那么多年来,我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家的老邻居─吴老太太当成一个
人,
所以,我一直对她保持了沉默。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把她与“人”字联系在一起过,但连在一起所组成的词
汇却是:“坏人”,“阶级敌人”。而在官方教育的开导下,我已经习惯于不把
“阶级敌人”当成人来看待了。只有当他们被改造好了,他们才能回到人们的行列
中。但上面又一直教育我们并且使我相信,“敌人”的本性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想起来了,我也有过一、两次对她说话的时候,但不是一对一,而是众人对着一、
两个人,是跟着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什么什么的。那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
她和丈夫一同被批判斗争,脖子下面挂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就是“打倒狗地主!”
一类的口号,然后在下面写上了他们的名字。现在回忆起来很奇怪,那时我根本就
没注意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只盯着那名字上面被打上的一个大大的叉,红色的,用
红墨水画出来的,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毙的人的名字上画的那个大叉一模一样,红
色的,很醒目。
这一个来月我一直拷问自己的灵魂:为什么二十多年来,对于吴老太太─这个我们
家的邻居,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我知道我错了,但我似乎不清楚我错在了哪里。
这两、三天来,我似乎看到了一点光亮:
我之所以保持了那么长时间的沉默,是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与官方保持完
全一致。当时上面反复宣传要“站稳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尽管年少的我不怎么太
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我的“政治立场”却一直站得很稳,就是一事当前,不问是
非,不思是非,无条件地站在党和伟大领袖一边,渴望成为“毛主席的好孩子”、
“(共产)党的忠实儿女”。因此,凡是上面视之为“阶级敌人”的人,不论这个
人现在表现得如何,不论我是否了解这个人的过去,我都要把他们看成是我的敌人,
与他们彻底划清一切界限。对待他们的方式,无论是轻蔑,贬低、挖苦、批判;还
是斗争,打骂,关押,枪毙,我都认为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
我对待吴老太太的方式就是:不把她当作一个人,更不必说当成邻居了。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这是我从五、六岁进露天电影院看电影时就问
大人的一个问题。一开始我以家长的标准为标准,然后是老师的,再大一点,就以
党和伟大领袖的标准为标准了。他们说什么是好的,我就相信那是好的;他们认为
什么是坏的,我就相信那肯定是坏的。
以人或者政党的标准为标准来衡量人,结果必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进而把
那些与我异心之人,视之为非人。
若没有上帝,我怎么可能把人当作一个人呢?任何的不同,无论是言语、种族、性
别、文化和观念的不同,还是社会地位、政治立场以及家庭出身的不同,还是宗教
信仰的不同,都可以成为一个堂皇的理由,使我将与我不同的人视为非人,并且作
践他们。
但是,人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
等,无论我与其他人之间,彼此的分别有多么大,但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点是共同
的:我们都是罪人。而无论一个罪人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另外的一个罪人也好,或
者一群罪人也好,他或者他们都没有任何权利不把那个人当成人,更不能以残无人
道的方式去对待他。人是上帝创造的,侮辱一个人,就是侮辱了创造他的上帝;践
踏一个人的尊严,就是亲手破坏上帝的创造。
我明白了,那么多年来我之所以跟着社会的潮流去作践自己的邻居,是因为我不相
信上
帝,是因为我心中不敬畏神。
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心中也是有恐惧的,但那是对人、对权力、对金钱的恐
惧。那么多年来,正是我心中的恐惧,使我本能地把“阶级敌人”视为自己的仇人,
并把仇恨的怒火与邪气倾泻到他们身上。因为若我不把敌人当成敌人,我就可能被
上面当成人民的敌人。而这是我万万不敢想象的。
我心中的怒火与邪气包含了什么呢?我看不透。父亲打我,我生气,但我的火不敢
往外发,只好压下了。邻居家的孩子大口吃糖,我馋,但我们家没钱买,我就是嫉
妒死他们了,也得把火憋在肚子里。还有,同学给我提意见,老师说这是为了帮助
我,我就是不服,但为了表现虚心,这口气我得忍住。但是,面对着敌人,就是什
么样的火我都可以发了。哪怕引起这火的,与他毫无关系,但我可以把以往压下的
所有的火,把过去憋在心里的全部的气,统统地倾泻在敌人头上。如此行,我不但
受不但任何批评,反而成了我阶级 斗争觉悟高的确切证据。
我心中最大的恐惧是对未来的恐惧,虽然我相信了关于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的美妙
宣传,但我对未来并没有真实的信心。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中,生活的劳苦从小就在
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听官方说,“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若实现,
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我信了。我认为绝对不能让这些地主、地主婆
的梦想成真,那样,不仅生活更苦了,我的脑袋也可能搬家的。于是,我仇恨一切
敌人。
我的恐惧和妒忌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家是地道的穷人,这使我在羡慕有钱人的同
时,却不自觉地妒忌一切有钱人。我下意识地认为,我们之所以穷,是由你们富人
造成的,即使不是你们今天造成的,也是你们的昨天、过去的剥削压迫造成的;即
使不是你造成的,也是你老子、你老子的老子造成的。所以,当我看到吴老太太被
斗争时,我不仅没有生怜悯之心,反而兴灾乐祸,觉得他们活该倒霉,谁叫你们过
去对穷人那么坏了,谁叫你们过去老是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上
面就是这么讲的)了,你们过去享够了清福,现在也该吃点苦了!
当一个人用冷漠,轻蔑,妒忌,恐惧和仇恨来对待他的邻居时,他是没有邻居的。
来到美国后,读过也听到过一个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耶稣讲的。一个人向耶稣
提出了“谁是我的邻舍”的问题:耶稣是这样回答的: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
得半死,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正好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
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末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了。只有
一个撒玛利亚人,旅行来到他那里,看见了,就动了怜悯之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
他的伤口,包裹好了,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他。第二天,他拿
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
耶稣讲完故事后也问了一个问题:“你想,这三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
的邻舍呢?”
那人回答说,“是那怜悯他的。”
耶稣说:“你去,照样作吧。”(引自〈圣经新译本〉)
“谁是我的邻居呢?”
这个我思索了许久的问题,终于从耶稣的话中找到了答案:邻居就是彼此关怀、彼
此和睦的人们。怜悯之所在,就是邻居之所在;爱之所在,就是邻居之所在。
按照耶稣的心意:“邻,犹爱也。”
2000年12月3日,夜11。20 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