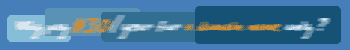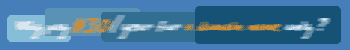我的老家在东北,离北朝鲜很近,有一个乡的名字就叫边门,后来为了中朝友谊,
就把它改成了一面山。这一面山是哪一面山,不晓得。但在老百姓心中,这一面山
大概就是凤凰山了。我们的县的名字就叫凤城。我们家所在的那个镇子,是县政府
所在地,在凤凰山脚下,叫凤城镇。但平日中大家都愿意用凤凰城来称呼我们的小
县城,并且,火车票上引的站名也是:凤凰城。
凤凰城是个大站,连从北京开往平壤的国际列车,经过凤凰城车站时都要停一下。
凤凰城车站挺老的,是日本人(本地人习惯称呼当年的他们是“日本鬼子”)占领
我们家乡时修的。我们那里的习惯,要是一个人乘火车到外地去,大家都叫“出远
门了”,家人和邻居自然地要问你,“多时候回来?”不管你归期长短,这一问,
总是要的。
我第一次自己出远门时,才十五、六岁,是到丹东去。丹东是我心目中的大城市,
与北朝鲜的新义州只隔着一条鸭绿江。我一共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慢车,有一站停一
站,七、八分钟就停一下。就是那样,我也兴奋得不得了,车厢内外,看什么都新
鲜,特别是看到车窗外的树木一排排地直往后倒,我恨不得大声叫起来,看哪!火
车跑得多快啊!
那次出远门,也有遗憾的事,就是火车票太贵了,要一块多钱。父亲一个月的工资,
还不到五十元人民币。
到美国了,一出门就开车,一开就总得个三、五英里,已经没了出远门的概念。外
出前,妻子和孩子爱这么问:你出去几天?时间(几天)的概念似乎取代了距离
(多远)的观念。二零零零年的五月,我从芝加哥到英国去传福音,飞行了七、八
个小时,又住下了二十多天,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算是出远门了。在英国,从
伦敦到爱丁堡到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到剑桥,乘的都是客车,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悠
悠岁月。不过,来来去去都是住在别人的家中。
在曼彻斯特,我住在了一对英国老基督徒夫妇的家中。他们不是我想象中古板高傲
的绅士,而是慈祥的长者,就像我的亲人一样。多年来,他们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
在曼城的中国人,他们教中国人学英语,照料中国人的生活,带中国人外出观光。
虽然书源很少,但他们夫妇却在全英建立了二十多个家庭似的中文图书馆。认识他
们的中国人(曼城中的中国人谁不知道他们呢),大被他们那至诚的爱心所打动,
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爱中国人的英国人,我也深有同感。在那里逗留的短短几天
里,我深深地为有这样的主内弟兄姐妹而感谢上帝。
到与他们分别的时候,我已经与他们恋恋不舍了。
离别的前一天早上,打扮得像一个农妇的女主人露茜上楼了,把我到英国这些天来
积攒的一堆脏衣服统统收拾到了一起,说,出门这么多天了,衣服得洗一洗了。我
这有洗衣机,很方便。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露茜家中虽然有洗衣机,但没有干衣机,只是在后院树起了两个架子,中间拴上了
一根绳子,请老天把衣服慢慢晒干。中午我回来时,我的衣服已经洗好了,一件件
地挂在绳子上,随着风,动来动去。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我们家也是这么晾衣服的,一看到衣服挂到绳子上,尽管大人一个劲地吆喝,到别
的地方玩,别把衣服弄脏了!但我和小朋友们偏不听,就在滴着水的衣服底下玩,
钻来钻去。水淋到头上脸上,高兴地尖叫。我们才不在乎脏不脏的,更不在乎弄脏
什么衣服了。
这样的情景,这样的乐趣,在美国已经多年不见了。
晚上我回来后,露茜已经把晾乾了的衣服放在了我的床上,叠得整整齐齐的,摞成
了一摞。还有几件衣服没干透,露茜把它们摊开,一件件地放到了卫生间的暖气片
上了。她爽朗地告诉我,别着急,一个晚上,衣服就全都烘乾了。这我相信,我在
国内时也曾这样使用过暖气片。果然,第二天早上,衣服不仅全干了,也全叠好了。
在房间内把东西打点好后,我就下楼了,到厨房和他们夫妇一同吃早餐。这时,我
看见炉子上有个小锅子里正在冒热气,里头煮着鸡蛋,就一个,是红皮的。怎么就
煮了一个?我有些不解,但也没问。吃饭期间,几天来从不劝饭的露茜,几次劝我
再多吃点,说出门前要吃饱,家常便饭,吃起来顺口。
以前我出远门时,我母亲也是这么劝我的。
吃饱了早餐后,我上楼把自己的行李拿下来了。这时,露茜递给了我一个大袋子,
里面装的鼓鼓囊囊的。她笑着对我说,…,你带上吧,是在路上吃的。今天你得坐
四、五个小时的火车,还得换一次车。
我一怔,心头好热,一时无语。
我默默地接过了老人手中的袋子,一提,沉甸甸的。过了一会儿后,我从心底说出
了两个字:“谢谢”,是用中文说的,她能听明白。但我知道得很清楚,相对于老
人那颗沉甸甸的爱心来说,“谢谢”这两个字,分量实在太轻了。
在火车上,我打开了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有面包,有火腿,有两瓶饮料和一瓶矿泉
水,还有水果:两个香蕉、一个桔子、一个苹果。此外还有一个鸡蛋,就是老人早
上煮的那个,红皮的。
看到这大袋子的食物,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出远门,到
沈阳去读书,得坐四、五个小时的火车。一大早,母亲就起来忙活了。我离家前,
母亲也是递给了我一个大袋子,也是装得满满的的,有自家蒸的馒头和小咸菜。那
时家里穷,买不起水果,就从地里摘了新鲜的黄瓜和西红柿。那时也没听说过世界
上还有饮料和矿泉水这些东西,母亲就用一个洗乾净了的玻璃瓶子,灌满了凉开水,
让我路上喝。当然了,还有好几个煮熟的鸡蛋,是自家养的鸡下的,也是红皮的。
从那以后,遇到我离开家出远门,即使有嫂子帮忙,母亲还是不放心,总是要亲手
把我路上吃的东西准备好,让我路上带着吃。我提着大包小包离开家门时,母亲总
是站在大门口看着我走。
我们弟兄姐妹一个个都大了,母亲就是这样看着我们一个个地离开了家门。
一九八五年夏天,母亲得了一场大病,半身不遂,一直病到现在。从那以后,一晃
十五、六年过去了,离开家门时,我就再也没有亲手接过母亲亲手准备的食物了。
我到外地参加工作后,有了点钱,出远门时,或者到餐车上吃饭,或者买些现成的
食品带上,至于吃的都是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反正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
带过那带着家的气息和泥土芳香的食物了。
火车是往剑桥大学方向开的。坐在车上,我慢慢地吃着露茜为我准备的午餐。一边
吃,我就一边想起了我的母亲,多年来,她也是一直惦念出门在外的孩子,我也想
起了当年一次次出远门的露茜。
露茜和她的丈夫道格拉斯是一对宣教士。
道格拉斯是宣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的四川,从小就立志向中国人传福音。四九
年后,大陆去不成了,他们夫妇就从英国去了马来西亚传福音,在那里度过了大半
生。
不回国门,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出远门,那不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隔离,更是语言
上、文化上、心理上和信仰上的巨大鸿沟。尤其是从一个发达国家─英国,到了一
个第三世界的国家,那种“远门”的感觉大概是我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但露茜夫妇
他们心中有天国,于是就把异国当成了故乡。几十年后回到了故乡后,他们又把两
颗爱心献给了来自异国的陌生人─中国人。
我突然又想起了露茜的三个孩子。有一次,我问起了露茜的孩子们的信仰,突然,
我发现她很伤感,她话音低沉地对我说,那些年中,我们夫妇老是在外面忙着传道,
只知道为主工作,没有能够很好地关心她们。我们没有很好地照顾好孩子。
从露茜的眼神中我读出了两个字:心碎。
那天我黯然了。我不知道说什么能安慰一个母亲的心,也不知道露茜在异国用爱心
照料过的那些孩子们如今都在哪里,还记不记得这个外国妈妈吗?在过年过节的时
候,他们打没打过一个电话或者写封信给她?在马来西亚那块热土上,有为露茜夫
妇祷告的人吗?这一切,我都没有问,也不敢问。
当我慢慢地吃露茜为我准备的午餐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几次想到了这一件事:在露
茜的儿女出远门时,工作繁忙的露茜,她有时间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一袋子食物吗?
当露茜带着长大了的孩子回到英国,她们夫妇是回到了故国,但她们的孩子们却好
像来到了一块陌生的土地,在学校中连朋友都找不到。在那个困难的岁月中,他们
孩子的那一颗颗幼小的心灵,能理解母亲的牺牲吗?能理解自己的父母的苦痛吗?
吃完了午饭,换了一趟车,我就来到了此次英国福音之旅的最后一站─剑桥大学。
在剑桥大学的那几天,我常常想起了将近一百年前从剑桥大学走出来的一批批出远
门的学子。不过,他们的“远门”,不是伦敦,巴黎,柏林,也不是罗马,而是隔
着千重山万重水的中国,是中国的穷乡僻壤,是连中国人自己也不愿意踏入的蛮荒
之地。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享受,不是为了淘金,探险,而是为了向中国人传福
音、为中华儿女服务。
这些昔日跻身于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与淑女们,剑桥的才子、名士,在远离自己的
国门和家门的地方作了传教士。
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末期了,大陆已开始对外开了一道细细的门缝,
但多年的教育仍使我坚信,这些来华传福音的基督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是
侵华的先锋。我从心里头恨他们。
我的这些观点,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七二年还乡务农后,不久,全国就又
开展了一场政治运动:“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孔子的简称)。为了深入批判林
彪和孔子,我找到了当时允许公开出版的所有的历史书。其实总共也没有几本。在
那些书中,当说到传教士的时候,一句好话也没有。而那里罗列的一切历史事实,
都是为了证明一个结论: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他们是帝国主义
的走狗和帮凶。从那以后,这个结论就记在我心中了。
五年前,当我归信耶稣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认识任何一
个基督徒、传教士,但我多年来却仇恨他们,仇恨基督教,仇恨基督?
我在我的〈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一书中不得不坦白地承认:那是充满了鄙视、
轻蔑、排斥和抗拒的心理,那是迷茫、失落、恐惧和仇恨的下意识。那是血液中奔
流的陈旧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是心思里分辨了数千年的华夷之辨:凡四
夷(“洋人”、“鬼子”)皆不如己,他们无知、愚昧、野蛮、心智未开、道德低
下。那是说不出口的受尽了蹂躏的民族耻辱感:被几个自己瞧不起的小对手打得一
败涂地,又不得不公开认输。那是倍受挫折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回顾祖宗的丰功伟
绩,充满了自豪;面对现实,则心怀不平、不愤而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我的心哪,你一直仇恨上帝,并与他为敌。
多少年来,我不明白官方的宗教政策为什么如此残酷,叫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横流。
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可能与此完全脱离干系,因为我心中那对上帝的无名的仇恨,
使我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侩子手的帮凶,使官方的政策显得顺乎“民情”,合于“天
理”,体现了“历史进步”的大潮流!。
我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要到遥远的异国去传福音?
我当然清楚地知道,耶稣留下了大使命,命令基督徒到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
但面向着那一片陌生而又遥远的土地,迈出家门的那第一步,难哪!
在我的书中,我问自己:将心比心,谁没有亲生的爹娘,兄弟姐妹,父老乡亲?谁
不爱养育自己的那一片故土?年轻人,哪一个不思花前月下,绵绵细语,情深意长?
人近黄昏,谁又不盼魂归故里、落叶归根?风华美少年,何人不曾立过大志,要成
就一番伟业,青史留名。但以戴德生、“剑桥七杰”为代表的一代代的英国的传道
士们,他们为了耶稣,就把这一切都舍了,有的,甚至最后连自己的命也舍了,且
埋葬在诅咒他们的异国的土地下,且有人把他们的墓碑也咂碎了,坟墓也推平了。
我想起了将近十年前自己出远门的那次经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家门这么远,
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终点站是美国的芝加哥。临行前,体弱的母亲强忍着
眼泪嘱咐我,孩子,能回来,就早点回来吧。呵。而八十多岁的年迈的老父亲则用
苍老的声音问我也问自己,孩子啊,爹还能等到你回来吗?
九五年回国探亲,与父亲别离前,老父亲问的还是同一句老话:孩子啊,爹还能等
到你回来吗?
终未能等到。
忘记是在哪一本书上读到的了,在十九世纪,在英国,一位慈母,听说自己的孩子
要出远门了,到中国去传福音。娘舍不得儿,劝孩子就在国内传福音好了。儿子也
舍不得老娘亲,但舍不得也得舍。为他舍命的主耶稣让这个年轻的传道士清清楚楚
地看到了:在东方那块古老土地上,一个个迷失的灵魂正在人生的荒漠上流浪,于
是,他还是走了。
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义和团动乱百年之后的中国人应当拍拍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当年来华的那些传道士
的绝大多数人,他们为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
是爱。
是他们对上帝的爱,使他们把万里之外的中国人看成了自己的邻居,并用基督舍己
的爱去爱这许多甚至如今还在恨他们的人们。
戴德生的话也许可以表达他们共同的心声:“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
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舍弃一
切。我们为上帝所作的,一点也不会过多。”
当自己为了福音而出远门的时候,愿戴德生的话成为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那我就
会明白了:我离开家门并不远,因为主慈爱的目光一直在关注着我。
写于 2000 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