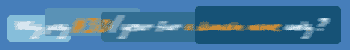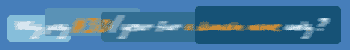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献给少年时代的夥伴们。】
一转眼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了。
二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放学的路上高音喇叭里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于是回到
家后就一个人守在收音机旁等待那重要新闻。结果呢,是最最敬爱的他老银家于当
天早上零时十分去世了。那年,我十四岁。正在肇东六中念初中。
提起这六中,当时有一套磕:新一中、红二中、(三四五中不记得了)。。。。最后
打狼臭六中。六中除了体育是本镇巨无霸以外,其余一概不行。校风极差,而本班
又是当时最乱的班。
第二天来到学校,大家都静静坐在自己的课桌后,往日的喧闹没有了。只有低声的
揣测。
“真能死啊?不是他不带死的吗?”
“你说,苏联会不会打过来?”
“你说,谁会当主席?王洪文还是华国锋?”
张老师进来了。看得出他眼圈都红了。张老师政治上是一贯紧跟的。因为一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他也没少整我。此人虽然不大地道,但他那俩姑娘却出落的如花似玉。
大女儿张立,高我一年级,是她们班的班干部兼文艺骨干。那模样,特像《英雄儿
女》里的王芳。二女儿小我一年级,叫什么我忘了。同样的水灵却更健壮,当时还
在少年体校速滑队,后来曾在日本破三千米亚洲记录。
张老师声音哽咽地说:“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记得当时身旁的郭金昌哥们,人称小老头,当时就抱头痛哭。兄弟我当时心想,这
小子不会是装的吧?细看又不像,人家眼泪都出来了嘛。郭哥们边哭边还叨咕著,
“我爹说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俺们家的今天。” 看他那声泪俱下的模样,我都差
点挤出几滴那什么鱼的眼泪来。张头接下来就是宣布停课,纪念毛主席。这就引出
了接下来几天的故事。
隔天,弟兄们再聚到班上的时候,已经是个个胸佩白花、臂戴黑纱了。一个个也突
然变得消停许多。张头端坐在前面念什么记念文章。本人听著听著难耐寂寞,就伏
桌在纸上画了一个小日本鬼子,拿把军刀。在小鬼子旁边是一个大大的墓碑,上面
注上几个字,“张瑞柏之墓”。叠成纸条递给身后的张瑞柏。这张哥们也是一神人。
长得罗锅八像的不说,还说话咳巴。所以他一人占有多个外号,如大笸箩、大舌头
等等。念书那是不中用了,但白白乎乎的见谁都能拉个上。这一日他也正在那边不
耐烦,见了我递过去的纸条,不加思索就把自己的名字蹭掉,换上了彬彬之墓的字
样,递了回来。
大笸箩奔就笨在这了。要递条你得瞅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呀。可正这功夫张头把眼睛
从那张破报纸上移开,想观察一下课堂上同学们是怎样寄托我们的哀思的。见我们
这俩的小动作,几步抢上前来,把纸条抢了过去。好哇,举国上下都在化悲痛为力
量,你俩小子还有心寻开心。大笸箩赶紧寻求解脱,“是彬彬先画的。” 得,把咱
哥们就这么出卖了。由于本人平时爱说个怪话五的,张头早就把我当个思想犯对待。
平日里就算表现好好的,他那眼里我也肯定在“腹诽”。这回抓住了,立即隔离写
检查。全班开批斗会。同时宣布,为了防止阶级敌银乘机破坏,校党支部决定,学
校民兵连要执行夜间值班巡逻。放学前到他那报名。
写检查对兄弟我是小菜一碟。哥们从小就写那玩意。记得第一次写是上小学三年级。
为了一点芝麻大的小事,老师非得让我写检讨书。那次可真是伤心透了。回到家还
大哭一场。不过,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再写就不伤心了。今非昔比,这些年
来写检讨已经成了习惯了。兄弟我唰唰唰写完,揣在兜里,该玩照玩。等下午快放
学了,拿出来交到张头手里。张头过了一遍:“哼,还算深刻,明天在全班宣读。”
看张头还算满意,本人开始试探著问:“今晚,我可以参加夜间值班吗?” 对这
事我本来是没抱太大的希望的。明摆著,刚犯了事,不把我当阶级敌人就不错了。
还指著我去抓阶级敌人、苏联特务?可张头瞅我一眼,竟点点头答应了。不知是想
给我个立功恕罪的机会,还是怎么著。至于我为什么想参加值夜班呢?一是也有点
想挽回点坏印象;最主要的还是觉著好奇。试想,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有
什么能比夜里跟几个同伴出来冒险更刺激呢?后来发现,那天报名的,除了一个班
干部外,剩下六七个全是平时班上的捣蛋鬼。
当晚,吃罢晚饭,跟老爸说要到学校值勤。既然是干正事,他当然是支持的了。于
是,我带著老爸当兵时的军大衣,和几个兄弟人模人样的来到了学校。
弟兄们来到学校时天已黑了。张头布置完就回他自己的值班室了。剩下哥们几个来
到教室里好不兴奋,一人卷一根蛤蟆蛄嘟,然后开始吹牛。东拉西扯一番直到支持
不住,决定睡觉。把课桌并到一块,就成了硬板床。那件军大衣设计的很科学,是
行军用的。白天披在身上,晚上拉链一拉就成了一个睡袋。领子上挂的帽子里还有
一个充气的枕头。铺上军大衣,躺在上面,虽然背胳得生疼,却也没一会就睡著了。
黑暗中忽然被摇醒,已是半夜十二点,该出去巡逻了。我们这七八个人,最小的是
我,十四岁,最大的十七岁。外面黑洞洞的,装模作样地拎著家伙式儿出来了。记
得我们还有一支步枪,没子弹。其余的大概拎著烧火棍、炉钩子之类的吧。前面的
赵守方打著手电筒,东照照、西照照的。我当时夹在这几个乌合之众中间,心里是
又兴奋又紧张,总想著要是有人怎么办?最好装著没看见,不然就我们这几条烂蒜。。。
也许是阶级敌银被我们这群散兵游勇给镇住了,反正他们没敢露面。我们也落得个
平安无事,回到教室里接著睡觉。一觉醒来,发现人都没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哥
们,他告诉我说那几个人犯事了。原来,等我们巡逻回来后,我睡著了。另几个家
伙睡不著,四个人围在一桌打起了扑克。没想到张头半夜三更起来查铺,把几个小
子给当场活捉了。这还了得,毛主席他老银家逝世,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你们几个
混小子吃了豹子胆了。全都给我圈起来写检查。
兄弟我一听这个乐啊。本来今天是要开会批斗我的。呆会就要到上课时间了,全班
一个接一个的发言,我还得虚心接受,多TMD恶心。现在好了,多了四个陪绑的。哈
哈,感情哥们我并不孤立啊。最高兴的是,大笸箩也是四人之一。嘻嘻,我就说嘛,
这种事哪能没他。看他们几个怎么写检讨吧。求我是不可能了,因为他们被隔离在
教务处的屋子里不许出来,从半夜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这四个人里,三个,大笸箩、宋平(絮老鸹窝那个)、周斌,是斗大的字写不出几筐
的。剩下一个却是个文痞。此人叫耿文政,原本肇东一中的红人,不知在那犯了啥
事,转到我们校来了。平时这小子穿一件黑白相间的格子衣服,戴一墨镜,梳一小
分头,在那年代特别显眼。这小子爱卖弄。每每拿起他那只钢笔在同学面前龙飞凤
舞一番。记得那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小子跳上前台发言,上来先来了两句
“雾满龙岗千嶂暗,天兵怒气冲霄汉。” 接下来劈头盖脸把邓小平一顿臭骂。把一
帮人镇的够呛。因为那时一开始还没直接点名,只是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
资派”。这小子则不然,不知是没这个政治嗅觉,还是要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居然
在接下来的批判稿中直呼邓小平的大名。这四个人圈一个屋里写检讨,最后那几份
检讨若不形散神聚那才怪了。。。
果不其然!等上课了,张头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宣布:今天批评彬彬的会改为批
判王张江姚四人。。。不对,是批斗宋张周耿。哈哈,哥们幸免于难。接著张头宣
布了四人的犯罪事实。然后拿出几张纸,对大夥儿说:我们来听听他们几个的检讨。
宋平:我一时糊涂,犯了错误。。。。
张瑞柏:我一时迷糊,犯了错误。。。。
周斌:我一时头脑极度昏迷,犯了错误。。。。
全班逗得是哈哈大笑。得。批判会也没开成。耿和我的书面检讨算通过。那仨人接
著折腾去。
一个月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银帮。兄弟我那天还打著大鼓上街游行哪。
又过了俩月,本人转到了肇东一中。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2001/9/10 于密西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