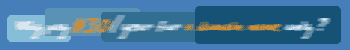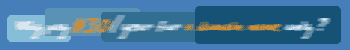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十三岁。我上学太早,所以那时我已是初三,而且我们都
已经考完了毕业考试,在准备升高中的考试了。我们学校是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子
弟中学,简称“公安中学”。有个小故事。市教育局开会,局长问:“二中来了吗?
实验(中学)来了吗?铁中(铁路局子弟中学)来了吗?。。。 劳改来了吗?” 我们
校长很生气,说“劳改没来,公安来了!”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学什么都轻松,特别是俄语。别人还咳咳吧吧
拼不清楚单词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读原版的玛雅可夫斯基了。唯独不喜欢的是初一
的《植物》和初二的《动物》,还有六四年教改后让学的《农村人民公社会计》,
总闹不清卖了粮,这款该记借方还是贷方。初二那年,校长可能受大比武的影响,
在学校大厅(我们校址原是一座展览馆大楼)把全校学生的成绩张榜公布,我名列全
校第二。第一是同级的女生李军,作文特棒。嗨!想想我们当年的作文题吧:《红》,
《绿》,《早晨》,《冬雪》,《无限风光在险峰》。。。学习好的孩子特得老师
宠,代数老师教诲我“你将来要去上科技大学”。因为年纪小,同学们也呵护有加。
苦恼的是个子太小,力气太小,最怕体育课投篮,“端尿盆”都够不着栏板。
中学三年间还有一个辉煌,就是演出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了。那个戏写当代中
学生如何胸怀亚非拉,为革命学习的豪迈情怀。是我们全年级三个班联合演出的。
主要演员是李军,我,邓元松,杨军,杨炳尊等。开头是录的广播剧,后来排成大
舞台话剧,在劳改局的南滩大礼堂演出。结果大成功大轰动。走在大街上,好多大
人能认出那个演戏的小孩 (西宁市南大街再往南,基本都是我们劳改系统的)。
(二)
中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三家村”开始的,大家写了不少“充满革命义愤”
的文章投到报社去。登不了那么多工农兵来稿,《青海日报》(大概是六月底某日)扩
了八版,专登投稿人名单。第一回看见自己名字变成铅字,挺自豪。接下来,开始
给老师贴大字报,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下一代。大厅和走廊都贴满了,又
在大厅拉上好多线绳挂大字报。大字报密密麻麻挡住光线,又得扯上电灯照明。因
有火灾危险,又倡议通宵值班保卫大字报,保卫文化大革命。
头一拨“红卫兵”没捞着当,家庭成分中农。等我爸专门从哪开出证明说出身实为
下中农时,已经早过了“唯成分论”那一段,任谁都可以套红布箍了。这是后话不
提。大串连可没耽误,先去西安,后去北京。十一月在北京一住半个多月,决定誓
死也等毛主席接见。岁数太小太老实,头回进京,那儿也顾不上玩,每天跑到北大
抄大字报。印象最深的是写“林彪是毛主席身边真正的定时炸弹”那个“小字报”
(不是在北大贴的)。红纸,金粉饰的边,工整的小楷。署名“红梅”。这张小字报,
很多写文化大革命史的书或文章中都有记载。我当时读的时候很害怕,在人群中大
气都不敢喘,我相信大家也都很害怕。总算等到最后一次接见,那次实际上干了两
天,头天在天安门,我们在接待站看转播,第二天轮到我们在西郊机场。车队过来
时,大家轰地都站起来了,车队一看乱了就加速。只见黄尘滚滚裹着毛主席和林副
主席跑了。大家都哭了,不是激动,而是辛苦了一天(我们早上两点就让负责接待的
解放军叫起来了,中午才走到机场)没看清楚特委屈。回到接待站,好多人连夜上书
中央文革要求再接见。陶铸哄我们说来年春天再来看毛主席。实际上,毛主席后来
在工人体育场又接见了一次参加接待工作的解放军,就再没有大规模的接见活动了。
虽然没看清毛主席,可跟李四光先生握了好几回手。李面色黝黑,下颚方正,说话
我听不太懂。问我从那来,想见主席吗?当时住的接待站是中关村的地质力学研究
所,李四光和另一位姓邹的副部长就住隔壁。李经常过这边看大字报,顺便看看
“小将们”。给李的大字报不多,语气也挺“人民内部”的。给何长工等部长的就
厉害得多。力学所的“走资派”是一个叫徐恩溥的老人,个子高高的,戴个蓝布棉
帽,整天扫院子。还有一位矮胖的二号“走资派”叫王克。我们还旁听了一次所里
的批判会,气氛还算温和。李四光当时很苦闷吧,每天下午和夫人一起出来散步,
各自手中拿个马扎儿,走累了就在路边歇一会儿,警卫远远地跟在后边。
另一大收获是见着真的电视机了。黑白的,锁在所里的大木柜里。那会儿还叫北京
电视台(后来才改成中央电视台),一开始演一个钟面,走到六点了,开始报新闻,
到十一点就没了。力学所的伙食还行。我们吃饭可都是付钱付粮票的,至多可以欠
帐,但后来欠条发票全寄到学校,一分也不能少。只有窗口放一小盆臭豆腐的汤是
免费的。我嗜吃臭豆腐就是打那会儿养成的。
(三)
再回到学校闹革命时,斗老师的风已经过去。老师们自己也组成了不同派系的造反
组织,互相吵来吵去。青海省的红卫兵分三大派。最老的是“总部”红卫兵,另一
派称“八一八”红卫兵,还有一派是“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红卫兵。“总
部”和“三司”基本是一事儿,被称为“老保”,“八一八”自命造反派,但也被
称为“老扒”,政治扒手是文革中常用骂人词之一。其实两派都在揪走资派,重点
不同而已。“总部”这边主攻省委书记杨植霖;“八一八”那边要打倒省长王昭。
不知为什么公安中学几派红卫兵的头儿都是六七届的。我和要好的同班同学最初都
在“总部”,后来不甘心受低年级的领导调遣,自己组织了个“独立团”,瞎胡闹
闹。中学生成立造反组织,当时主要是要两个东西,一是扩音机;二是自行车。劳
改局有的是好自行车,好多老“三枪牌”的(英国造)。我就是那会儿学的骑车子,
腿刚够着脚蹬子。
六七年新年过去不久,解放军开始支左。先是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一个连一个方
队,正步行进;还有长长的车队,全部新军车,从古城台逶迤到火车站,壮观极了!
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勒令占据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退出去。二月二十三号,军
区侦察连的神枪手几发点射打哑了所有的高音喇叭。然后部队从报社北门攻了进去。
杀人如麻,包括十多名“首都三司”的红卫兵。我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人打死了,
衣服也能打飞?一个青春年华的女红卫兵,躺在浸血的废墟上,上身全裸着,两个
雪白的乳峰,僵硬地质问着高原的天空。一个月以后,中央给“八一八”平了反。
支持“八一八”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一度跃升到人民日报报导出场序列的第
五位。刘和赵的女儿,跟你嫂子当时在军区子弟小学同一个班。你嫂子对她们两个
反复经历从公主到灰姑娘的角色转换,印象非常深刻。
“八一八”平反之后,我们属“总部”派的组织都作猢狲散了。军宣队已经进驻学
校, 正式领导我们“留校闹革命”。低年级的后来好像还真上了几天课。毕业班的
除了组织学习批判刘少奇,基本都在“逍遥”。“留校闹革命”一直持续到六八年
夏天,但两年时间留下的记忆几乎是空白。好象到支左部队的营房参观过,看那个
排长张任武投弹八十六米。学校组织起来游过几次行,欢呼最新指示发表。没受任
何人指使,我心血来潮,独自写了一问,二问,三问校长的系列大字报,批判资产
阶级办学路线。还有开大会庆祝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每逢开全市大会时,我们
爱溜去省话剧团那边看张亮。。张亮是名演员,文革前演过《革命家庭》(饰儿子),
《林家铺子》(饰寿生)等电影,文革后贬到青海。我们看真人长得什么样。
在那两年时间里,“留校闹革命”的同学,有的练二胡笛子,有的玩自制的火药枪,
有的刻像章(木刻版),有的学配钥匙。我看了很多书,福尔摩斯之类的。跟我们班
两个大同学学过“飞虎拳”。某晚,一个醉汉在南大街向我挑衅,我一拳敲出他满
脸血花。继续装半导体收音机,到超外差式但怎么也不起振。开始学抽烟。用弹弓
故意打碎过一个临街玻璃窗。跟几个大同学去南山家属院偷过一只鸡。有时深夜一
夥人骑着自行车,从寂静的街道上喧嚣而过。革命“造反”的号召充分唤醒了我们
人性深处的野性。没人管的日子,感觉象断线的风筝在飘荡,确实是自由的,但不
知何处是着落。就这样下去么?从激动,兴奋,到迷惘,我长了二十多公分,有胡
子了,也出了点胸肌,身板直溜溜的。我从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变成一个令老
师和军宣队头痛的桀傲不驯的青年人。
(四)
六八年夏天,“留校闹革命”结束。有几个同学当兵走了。与全国范围内已开始的
“上山下乡”一致,相当一部分同学是回到或安排到农场参加工作;家在西宁的也
有走门路进工厂的。剩下一批还要读书的(:-))分配到有高中部的学校。我分到西
宁市十五中。这个学校以前是个中专师范。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总部”和“八一
八”红卫兵的司令都出自该校。革委会成立之后,有了政治资本,就改中专为正式
中学,另辟初中部和高中部,似乎升了一个档次。“复课闹革命”复了几次,学生
没心学,老师没心教。运动还在深入发展,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自己就要倒霉。原
来那帮中专生里,有几个是“八一八”司令部有名的打手。入校不久,高中班就发
生了这么一件事,家在省委大院的同学杨小平,参与掩护,协助一个“走资派”的
“臭老婆”,跑到北京告状。事泄后,那名同学被他们打得好惨。对同学尚且如此,
更别提对老师中的“牛鬼蛇神”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一个干干净净的体育老
师,让他们突然揪到台上,顷刻间就被打得稀烂,面目全非。
文化课学得有一搭没一搭的。学农学工可是一点不马虎。开学后,很快去海南州的
一个部队农场参加秋收。跟解放军干活的最大好处是吃得好,吃得饱。连队的学毛
着积极分子给我们作讲用报告,说“五七指示”是毛主席绘制的雄伟的共产主义蓝
图。我无可奈何地想,即使将来“大学还是要办的”,生活也就是这个模式了,以
这个为主,再来点别样。。。 不过这个积极分子好象不太得人缘。他去食堂帮厨,
累得满头大汗,出来一盆凉水把自己给浇晕倒在地。我们学生都感动得不得了,却
有几个老兵对我们说“别相信他那装样”!老兵们说该标兵正在积极争取入党,这
样就可以提干,脱离农村,他经常假装说梦话,比如“指导员,这危险,我来干”
之类的。
学工是在工宣队进校之后,去工宣队来自的大通煤矿。女生分在电工班,在井上给
矿灯充充电。男生全部下井,有在掘进队的,有在采煤队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把最
恐怖的地方叫“地狱”,因为它在地底下!采煤队的活儿是在低矮,不容直腰的工
作面上。顶上经常有煤块掉下来,安全全系于张在头顶的铁丝网。我们去的还是安
全条件最好的小煤洞坑口。有一回,升降罐笼坏了,我们不得不走好长时间从陡峭
的通风道出来。当我最后看见地面上万家灯火时,我突然觉得我是那么热爱生命,
热爱到不是在那个岁数应该有的程度。学工的收获是使我觉得工人阶级其实根本没
有毛主席说得那么伟大。就是干活挣钱(矿工的收入与下井时间紧密相关)呗,爱说
下流话,还给我们宣传迷信(井下闹鬼的故事,很多很多)。除了要求福利,他们并
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更别提世界革命了。那一阵,有一大批北京矿院,西安矿
院的大学生分到大通煤矿,也是统统下井,至少干一年。我住的(四人)宿舍就有两
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宋玉光,吴景川)。他们对我很好,象大哥哥一样。老吴那时不
知在北矿惹了什么祸,好象还戴着个“反动学生”的帽子,每月要对党支部交个思
想总结。那时刚刚兴起“早请示,晚汇报”,一表演,我就想笑,他俩也冲着我笑。
我天天跟着他们一起下井。从上班起,一刻不停地把溜槽里的煤块儿往下捣,煤最
后流到运输巷道的矿车里,被运到地面上。不停地捣呀,而且是倦曲着身躯,只有
放炮的时候才有片刻休息。一个月下来,我臂力大增。掰手腕把我最有劲的,大我
好几岁的一个朋友赢了。
高中最后的日子是在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度过的。我自认音准,但不会
发声。我农场小学的音乐老师,曾经耐心地辅导过我一个晚上,教我怎样放开嗓子
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到底没有成功。长成大人了,其实对唱歌跳舞有点鄙视,
觉得不男人。工宣队的逼了几次,只好参加了。顺便说一句,你嫂子也是宣传队的,
她那时上初中。我基本是个“龙套”,搀在队伍里瞎起哄。跳舞不舒展,找不着那
种“看我多优美呀”的感觉。刚上台,真不知手脚往哪放,还出了不少洋相,把导
演和工宣队的给气的。好在人不算笨,几套表演老重复就熟练了。我们不停地在工
厂,部队,农村演出。歌颂党的“九大”,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红军不怕远征难,藏族人民心向北京等等。六九年夏天,宣传任务告一段落,
大家一起去人民公园在百花丛中合个影。宣传队解散了,我们这批学生按年限也到
了“高中毕业”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一个巨大的魔影,正伸展黑色的翅膀,无声
无息地向我飞来。
4/8/2001
《青春祭》(下)
聊《青春祭》--阿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