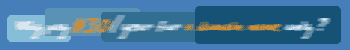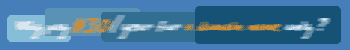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一)
“同去同去,造反了”的召唤带给我们少年的兴奋是极其短暂的。伟大领袖亲手点
燃的熊熊烈火,很快就把千家万户烧得焦头烂额。再神圣的革命,一旦锋芒直逼自
身,你就难以向往了。当革命从“破四旧”陡地变成揪“走资派”时,我的许多同
学和好朋友的父母纷纷中箭落马。
鲁西安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母亲时任劳改局政治处主任。运动开始,变成“走资派”
加“叛徒”。武江平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爸爸是劳改局局长。运动开始不久,因
“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判刑入狱。他是全国为数寥寥的,经正式法律
程序判刑关进监狱的高级干部之一。我所仅知的类似例子,就是《鸿》的作者的爸
爸,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我的老爹只是农场一般干部,不够当“走资派”的资格。
他是到“清理阶级队伍”时才倒霉的。罪名大体是当年他在游击队里,有三个最要
好的同学是拜把子的兄弟,是“反革命小集团”。解放后,他在法院办案时还把其
中一人的舅舅“高抬贵手”了一回。
父母挨斗,子女感受到的是羞辱。我们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开始迷惑,开始怀疑,
开始抵触。难道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夜之间就都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难道还有那么
多的待深挖的反革命?中央是否有人浑水摸鱼,为自己夺权?有“联动”的朋友到
西宁躲风来了,讲了许多北京的故事。一旦知道“旗手”是演员出身,她的光环突
然变小了三圈。我有个很奇怪的偏见,即不相信演员搞政治。所以后来看里根,总
觉得他是在白宫“演”总统,而不是当总统。鲁西安是最有“叛逆”思想的。“既
然可以‘怀疑一切’,为什么不能反中央文革”?他深思熟虑地对我说。
在“逍遥”的时期,我们还认识了外边的新朋友,命运相似的朋友。章继明,章耀
明,很受我崇拜。他们有武功,会唱很多老京戏。他们父亲是省中医院的院长,东
北抗联的卫生队长。除了“走资派”的罪行之外,还说赵一曼是他出卖的。医院造
反派批斗老爷子,兄弟俩抄起大棒子冲进会场救人,让造反派捆起来,一边篮球架
上吊一个,老爹心疼得直掉泪。外贸局家属院的邹立亮,滑跑刀滑得特棒。涂庚生,
围棋下得够段位。他们的父母也都在“牛棚”隔离。大家处境相似,就爱往一堆凑。
凑到一起,不难想象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会怎样理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每次见面,免不了会说些“小道消息”,“反动话”。有一回,好几个朋友不约而
同都推了光头。大家见面哈哈一笑,“这不成了光头队了吗”!
我们有个初中同学叫魏建国,外号“秃子”,身世很糟糕。他母亲解放前受了流氓
的侮辱怀了他,他父亲出于同情与他母亲结了婚。五几年,他母亲就因病去世了。
父亲再婚,生有一个弟弟。魏建国从小顽皮,不服管教,学习也不好。认为自己是
后妈,跟家里关系很僵。文革中,他爸实在管不了他了,遂把身世告诉他,他成了
孤儿。公安中学分配时,他没去农场。户口,粮食关系都在兜里揣着,东家住两天,
西家混两天,成了流浪的黑人。他想走体育招工的路子到厂矿工作,但他的篮球也
不是太好。实在不行,就下乡吧。他想约我们这些朋友再商量一下。
时间:约在“九大”前后, 某晚上
地点:外贸局家属院, 邹立亮家
内容:讨论“秃子”今后的命运
“会议”主持人:就是我
我自封大会“秘书长”,并煞有介事地作记录。一种小孩儿“过家家”的心理吧。
“现在开会了。请大家拿出《修养》来”。众哄笑。
在那个年代,按开会程序,应该拿出《毛主席语录》来,首先学习“最高指示”。
都是自己哥儿们,所以敢出风头说个“反动话”。商量的结果是再等等,可能最近
哪哪哪儿还有招人的机会。害怕一旦下了乡,就再不容易上来了。
大家散的时候,章家弟兄先出门。我说,
“请列宁同志先走”
《列宁在十月》的台词,对吗?用在门口很不失幽默,对吗?其后的历史,要我,
我的好朋友们,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朋友们,为了这个夜晚我这些轻浮的,哗众取
宠的言行付出了太沉重太沉重的代价。。。
(六)
“秃子”的流浪生活没有继续多久,很快就出事了。他翻窗进了一户人家,盗窃几
十斤全国粮票和不多一点钱。案是即刻就破了,床单上给人家踩了那么大个回力鞋
脚印!当时政法系统全部都在军管之下。办案人员不满足仅仅破一个小小的盗窃案。
他们了解到“秃子”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都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即大部分为
“走资派”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子女。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
节胜利的时候,在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时候,
如果挖出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将是对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
部作出的多么献忠心的行动啊!
半月之后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学校革委会副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两名公
安局的在那等着我。
“你认识魏建国么?”
“是我同学。听说他偷东西给抓起来了。”
“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你有些什么东西要交代吗?”
“我?我又没有偷东西!”
“你不要假装镇定”,对副主任说,“你看他这个人表面上还挺镇定,其实我们都
掌握了。”
“... ...”
“你们有个组织叫什么名字?你们最近开了个什么黑会?”
“?!”
“你要老实交代!”
“... ...”
nbsp;
窗外灿烂的阳光突然变得很刺眼。我意识到形势不妙。不是小不妙,而是大不妙!
恫吓,启发,斥责,诱导...你们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叫“光头队”;你们的组织
结构至少有“秘书长”和“列宁”;你们的思想纲领是刘少奇的“黑修养”;你们
最近的行动就是破坏上山下乡;你们...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在青海省
全省名躁一时的“光头队”反革命大案。规模有多大,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听说牵
涉到四,五十个青少年,绝大部分是我不认识,或根本没听说过的人。因为他们非
常想挖出一个囊括省委大院,省军区大院,和省公安厅大院的反动组织。最理想是
再找到后边操纵的“走资派”的黑手。
从那一天起,我觉得胸前背后被镌上了无形的红字,归入另册。那一年,我才十六
岁。美国人登上了月亮,中国正在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青海情况特殊,那一届的
毕业生全部分配三线厂矿。我有“要案”在身,前景岌岌乎殆哉,惶论分配。当大
家昂首挺胸跨进工人阶级的队伍时,我卷起铺盖灰溜溜地回到草原深处的农场家中。
在那个人生最糟糕的时刻,只有两件事可庆幸。一是那帮中专打手已经分配离校,
所以我没受皮肉之苦;二是,学校开大会宣读省革委会转发《关于西宁市城中区公
安分局破获“光头队”反革命集团案的通报》时,我人已离去,所以未受上台示众
的羞辱。最惊愕的该是我们文艺宣传队的那些同学。你嫂子哭了, 说“不相信,不
相信”,那时我们还是纯粹的同学关系。
(七)
回到家中。父亲刚从“清队”中解脱,按“人民内部”贬到底下中队去作管教。我
出事的消息在农场一阵风似地传开了。作为反革命组织的骨干成员,是否会逮捕判
刑,殊难逆料。老爹一辈子硬气刚强,夜里悄悄地为大儿子哭了。那个年代,一旦
服刑,不管什么罪名多长刑期,都意味着一个人的一生报废了。
农场有许多从小一起长大,现参加工作了的朋友和同学。开头我还能去串串门,很
快大家就尴尬地躲避我了。不是他们不够意思,而是我前脚走,后脚就有领导谈话。
敲响警钟,划清界限等等。农场中学也把我的“事迹”加上充分的想象,当作“活
教材”在学生中进行教育。搞得两个弟弟好抬不起头。我只得噤声屏息,足不出户。
那些日子,除了挑水做饭,读完了十卷新版的《鲁迅全集》,包括两本很难读的译
文集。再就是用木板,硬纸,橡皮筋作玩具。做得最漂亮的是一个军用吉普的模型,
上足橡皮筋可以跑二十多米远。那个小吉普车我保留了很长时间,作为那些日子的
纪念。
经常黄昏独自坐在一座破窑上,久久地目送一轮火红的落日西沉。草原上有几缕轻
袅的黑烟直直地飘向晚霞。黑黝黝的大山后边是五彩绚烂的天幕,慢慢地退色,变
成青灰,最后倏尔就与大山融成一体,唯有星光还能勾勒出山的轮廓。心中空荡荡
的。正是走向生活的时刻,一抬脚,却发现面前是深渊万丈...新读的鲁迅,最
记得的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句。从那时起,我跟毛主席开始疏远
了。七年以后,八亿人泗泪滂沱哀悼伟人去世时,我也在吊唁的队列中哭,我觉得
我的眼泪很虚伪。直到听到一个长辈的解释才明白,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在“借别人
的灵堂,哭自己的悲伤”。
在家的日子,绝不是闲居,象我后来在履历表中所填那样。虽然我没有象鲁西安,
邹立亮那些朋友被他们的单位多次揪斗。“专政”的利剑却始终悬在头顶。三天两
头,就有农场军管组电话打来,命令立刻到场部接受外调的审讯。每次接到这样的
电话,妈妈就非常紧张,问“要不要带行李”?
外调人员形形色色,按规矩都是两人一组。通常一个唱红脸,轻声细语地,千方百
计地把你往陷阱里引;另一个唱白脸,又拍桌子又踹椅子地吓唬你。最可恶的是农
场的几个看着我长大的叔叔,也在一边吹胡子瞪眼。我申辩,我们确实没有什么
“组织”。“秘书长”一说纯属恶作剧。他们排出一沓一沓的口供。“看你们同夥
都交代了。你顽固不化,最后只有你进监狱”!在那些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会
“进去”的日子里,军管组有一个姓师的副教导员曾对我说,“小鬼不要害怕。这
次的外调是了解武江平情况的。你们年纪轻轻犯了错误,说清楚就好,不要背包袱”。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个温暖的安慰。
去场部的路上,有一条深深的大沟,到那儿自行车只能推行上下。记不情是第几次
又被外调的折磨了一番;手指鲜红在交代材料上摁满了指印。回家路上,气喘吁吁
地爬上大坡,随手把车子扔在一旁,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天上有白云苍狗,被风追
逐得无处安生。我满腔悲愤一声长嗥。那吼声,在空旷的草原上是那么微弱,那么
无奈。“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我想。
一年以后,那帮家伙到底没有能找到“反革命组织”的确凿证据;加上一些朋友的
父母陆续得到“解放”,重新掌握了权力,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案,遂不了了之。我
在农场就地参加了工作。虽然“反革命组织”不成立,各人的“反动言行”还都在。
在档案里,与我同行。
(八)
当年在农场参加工作的,主要是开拖拉机,或者去修配厂当工人,极少数幸运儿能
去开汽车。我赶上的那一批却是个新鲜事---糖厂。文革中兴过五小工业,比如小水
电,小水泥,小化肥什么的。这小糖厂的概念是当时轻工业部在“不吃进口糖,气
死帝修反”的口号下设计的。以甜菜为原料,日处理三十吨的规模。全国(北方)仅
试四个点,分别是河北静海;山东莘县,新疆建设兵团(库尔勒),和青海劳改局(先
在塘格木,后迁浩门农场)。从甜菜根(糖萝卜)里把白糖提炼出来,要经过挺复杂的
工艺流程,有切丝,浸出,过滤,蒸发,结晶,和分离多道工序。我是唯一档案有
问题的人,所以最初到外地培训时,我的岗位是……烧锅炉。又因为我是唯一的
“高中生”,所以又不得不让我去学化验。另一位是农场书记的女儿,挺努力但搞
不清楚什么是元素。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了好多年,接班人从林副主席变成了王洪文;邓小平也复出以
“三项指示为纲”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过去,运动好象只在两报一刊的社论
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气吞山河的朗诵中。人民疲倦了,不管是被整的,还是
整人的。有很多人民在养热带鱼,包沙发,打家具。
我们辛勤地劳动,从建厂房,安装设备,到开榨出糖。第一锅白糖作出来时,也挺
兴奋,有事业感。但糖厂是季节性生产,每年榨季不过两三个月。其余时间,除了
政治学习,有时还得下大田劳动。闲暇时候,打打篮球,洗洗照片,串门喝酒下棋
聊聊天。为了工作,自学了一套四本的中专化学课本。想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但终于没有读完。养过一条狗,从狗崽养大的,后来不让养了不得不让人击毙……
四年过去了!就这样在雪山脚下过一辈子么?我极惶惑,极不甘心。
大学恢复招生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工农兵学员”。“同案”的朋
友涂庚生竟然成功地从插队的公社被推荐进了青海师范大学。可以想象上大学对我
们那时的青年该有多大的吸引力啊。档案里的东西仍然背着,只能羡慕别人的幸运。
七四年的大学选拔突然要加考试了。我兴奋地报了名。那时是按系统招生。青海省
劳改局有一个吉林大学化学系的外地名额!考试得地点就在母校“公安中学”的小
学部。文化课的测试实在太简单了。政治倒稍微要用点心。比如林彪路线的实质是
什么,“欧安会”的战略目标如何等等。全系统十来个考生,很快都有了着落。我
档案里的东西仍然在作祟。劳改局教育科的主持人实在为我的成绩可惜,暗示我自
己再去找找吉大招生老师。
招生老师住在西宁宾馆,省交际处所在地,是青海最好的接待单位。文革前,邓小
平吃天鹅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一共杀了两只)。我走进老师的房间。老师人很干净,
戴眼镜,着青灰色干部服。我已经完全想不起他的模样了,依稀留着点拜见了张春
桥的感觉。因为老师无表情,话语极省俭,很多意思都用眼神表达了。
“老师,我想上学读书。”
“……”
“老师,如果是因为‘光头队’的问题,那早已有了结论,我们不是……”
“嗯------哪! 你父亲是不是也有历史问题啊?”
“……?!”
那一年,另有一个年轻人,成功地为自己的命运抗争,走进了大学门。他叫张铁生,
在全国都出了名。说实话,除开一点酸葡萄而外,我是真心为他高兴的。
生活仍然在继续,革命也还在深入。从批林批孔,又批到水浒宋江了。谁也说不清
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还有完没完。但见老人家日益衰竭下去,张开的嘴角已绷不住
口水流淌了。
大约因我工作踏实卖力,居然可以吸收我入团了。再后来,居然身着警服腰别手枪,
全国跑着去执行任务去了。那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北到本溪, 南至鹰潭,东抵舟山
群岛。河南江苏两省几乎是挨着县转过来的。一次乘青岛-西宁的快车回青海,在餐
车里听几个下班的列车员大侃西宁风情(那趟客车是济南局的),“哈!西宁的流氓
组织叫‘光头队’,清一水的秃头,大马靴。打起架来,二话不说就上刀子。在大
街上,看上那个姑娘就抢那个姑娘……” 三人成虎,真假李逵,我唯有苦笑。他们
绝想不到这名字害得我们吃了多少苦头。也想不到这个正在吃饭的警察就是大名鼎
鼎的“秘书长”。
风雨兼程中,看着刷有“‘文汇报’是谁家喉舌”大标语的列车南下北上;总理走
了, 朱总司令也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堆成了山; 大地在颤抖,好象空气在
燃烧;唐山顷刻夷为平地;伟大的导师在九月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人帮”
被粉碎的时候,我正走在甘肃的一座大山上。同行的公社干部告诉我,县上传达了
文件,江青王洪文他们犯错误了。我的心突然加速跳荡起来,眼前的山川突然变得
那么明亮,步履轻松了好多。我隐约感觉到彻底把身上这个政治黑锅摆脱的日子该
不会太遥远了。
七七年夏,好友鲁西安的母亲来信把我从南京召了回去。说今年大学又恢复考试了,
你还是应该再试一下。按地区,我参加海北州的考试。当年考题,现在图书馆都能
查着。青海的题不难, 自我感觉各科都答得不错,化学尤其有把握,好象是一分未
丢。后来有朋友在省教育厅核察过,我成绩确是地区第一名。当时特珍惜这末班车
的机会(当年还有考生年龄限制), 志愿不敢报太高,又不甘心放过重点,所以第一
志愿只报了个兰州大学。没想到还是被吉林大学给先挑走了。我妈说“是不是那个
老师又回来找你来了”?那年我们家一次走了三兄弟,老爹老娘脸上都是光芒万丈
的样子。
在七七级新生入学座谈会上,我讲了两次考试的情况。主持会议的团委陈秉公老师
很感兴趣,说可以问问七四年谁去青海招的生。我也很想再见见那位老师,叙叙我
与吉大的缘份。后来开学一忙起来,就再也顾不上这事了。
【全文完】
4/22/2001
《青春祭》(上)
聊《青春祭》--阿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