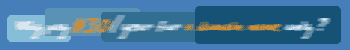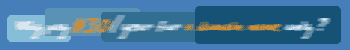1978,深秋10月的今天,从内蒙通辽到长春的火车徐徐驶进那个沾日本味儿的洋式
车站。出到站外,我到处找吉林大学接站的旗号,啊,在左边,“我来报到。”
那时的我大概是这么个模样吧:从秃子长起来的寸头,身上是母亲给做的毛式卡奇
布蓝制服,已穿旧了,脚上好象是双解放鞋 (冻天有双军大头鞋,哥哥给的,但记
不准当时登上没有), 还没近视到带眼镜。这时的我虽年龄跟一些今天的‘西装、
麻将’ABC相仿,但经历不大一样。。。
真正学了一点课本知识还是在乾安县所学公社大布苏大队的大布苏小学。那里有我
的穆、宋二位老师。他们是夫妇,师专毕业。他们给了我一个起码是功利角度的榜
样。知识分子在那种偏僻乡野之地受人的尊重跟我过去在一些大学校园里见到的很
不一样。再者就是给了我自由,不大过问我自己课堂课间做什么。记得一次教我算
术的宋老师问我,“将来想当啥呀?”我按心里想的实话说“要是有个图书馆能去
当扫地的就好了。”那时候,其他想干的事就我这‘德性’没太大的戏,就这也不
是说想有就能有的。
后来。。。后来在内蒙我从‘盲流’变回应考生身份又恶补了不到四个月就上阵考
大嚣了:)) (跳着点,够晚了:)。不怕笑话,我只考了364分。但那暂咱还挺牛,
明年再来,跟家里的‘合同’是得管饭。这个物质基础是我跟拉拉这样的才俊竞争
中的不公平优势,我不以此为骄傲。的确,在乡下就天资而论能跟我这样的争的多
的是。
报志愿吧,我就报了仨,俩是蒙着整的,尽管第一志愿确是吉大物理系但我的分够
呛,后来看是缺个二十三十的。有一个是我瞄的:大连工学院造船系,我喜欢海,
并且由于家里原因对那所学校比较熟悉;考分也应该够。又顺手在是否服从国家分
配栏填了“本人不服从国家分配”,我怕硬塞个地方让我去。
再后来。。。我的档案成了‘死档’,据说跟答的那句话不中听可能有关系。但为
什么要问?幸好吉大少数民族地区名额不满,降20分分数段找找,假少数民族可能
也行吧,实在不行看看。。。哲盟师院去招生的崔老师的夫人是教我物理的,她是
蒙族,她对我的种种鼓励是那段时间里非常宝贵的心理帮助;还有一位哲盟去的招
生干部也帮了大忙:跟一位上级强调了象我们那种地方出一个这样成绩的多么不易
。。。 阴错阳差我就今日站在了报名处的桌子前面。
把行李装上车,正撞上一沈阳来的法律系新生跟啥人吵架,几乎动手。这位我把他
名儿忘了,但后来好象也在美国。他的棱角分明的面孔给我挺深的印象,应该是个
好律师。
八舍,二楼,几号来着?上楼左手第一门是厕所,我们是第三门。这脑瓜筋,完了。
进门来只有汽车厂的老康大哥在屋,这位是我的烟友、酒友、还是亲戚 (开始不知
道,我的亲堂姐跟他的亲堂兄是夫妇,后来老康大嫂从名字看出来的,堂姐‘萍’
跟我就差一字)。 我在把门的下铺。各位起夜的给我的麻烦远不如那些相互打听考
分的。每次感觉上我都好象先来个立正、上身前倾:弊人是被当少数民族照顾进来
的。我是班上的倒数第二名,第一名也是我们内蒙来的。作为参照,我们班老于大
哥是那年的吉大新生最高分 448;我们屋的老孙(玉琢)大哥也是四百一十几分、省
内吉大新生最高。当时大的32岁小的16岁同室上课,中间就是咱这样的几毒都整过
的混混。不管怎样,咱记着母亲的话:翅膀够硬了,飞吧。我这就开始了实现第一
学期只求及格,剩下时间扑向文科书库的计划。
当年去招生的孙密文老师看我二年级以后认真求功名了,跟我提到过:最近你还上
挺快,当初是照顾了你一把。那以后就不象第一年那么放任了,实际上也未必一定
是福,但的确使我今天能在大洋这边敲这些平淡的往事。对于个人,报志愿那次是
我第一次公开对国家机器说“不”。
10/13/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