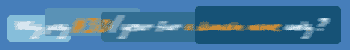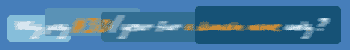他至少比我大二十岁,但是由于他的岳父和我的父亲是同事,我
就叫他姐夫。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和我们家住邻居,只记得
在我还分不清“浪打浪”还是“狼打狼”的时候,就常在他家和
他一起唱“红湖水”了。他不苟言笑,再加上身居县委招待所所
长之职,虽然只是个二十一级干部,但在那六六三十六户的小院
儿里也算是个大官儿,所以大人孩子们都对他多敬而远之。我也
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就不怕他,而他与我一起时话也特别多,在我
眼里他更象个顽皮的大孩子。也许因为我叫他姐夫,也许因为他
喜欢我那不失顽皮、而又少年老成的样子,我们俩在一起时总有
说不完的话、断不了的笑。他打小儿没爹、没妈,是个放牛娃,
解放后先后在合作社、县人委当通讯员,五几年扫盲时学了几个
字,以后一步一步的就当上了招待所的所长。也许是工作的关系,
他喜欢喝酒、酒量也好,朋友也特别多。招待所的那些年青人与
其说是他的属下,还不如说是他的酒友、哥们儿。文革中他也被
挂牌、批斗,但是从来没受过皮肉之苦,到是常常有那些白天批
斗他的造反派,晚上到他家来喝酒聊天儿、通风报信儿。
不需要上课的那些年,我几乎是天天黏在他家打扑克,对主、升
级、仨拿一和争上游(那时不能叫抓娘娘)的功夫样样炼得炉火纯
青。到吃饭时我要回家他也不会留我,知道家父不准小孩子在别
人家吃饭,不过要是吃点儿换样儿的,他准会打发孩子给我送过
来一盘儿。
他的严肃邻里们尽人皆知,可他的顽皮却只有我真正领教过,而
且还上过不大不小的当。一次饭后他对我说:“今天我学了一个
戏法儿,叫千里眼,只要你把一只沾足了墨的笔放在嘴里刁着,
闭上眼睛想看啥就能看到啥”,“真的?我不信”,领教过不少
次戏弄,怕又有诈。“着次保证是真的,想你妈你就能看到你妈。
就连你从来没见过、将来要娶的媳妇都能看到,你不想看看她是
不是一脸麻子?”。这最后一句连威胁、带利诱,把我弄得心里
直痒痒。“不信,你敢跟我割个东儿?”,嘴虽然还硬,但心已
经上了贼船。“敢!”,“割啥?”,“我要是输了,将来你说
不上媳妇我给你找”,他又借机开我的玩笑。“不行,你要是输
了以后打扑克我的枕头你顶着”,“行!”。那年头儿虽然不读
书,但笔墨可到处有。我拿一只墨笔,沾了个汁饱汤圆,放在嘴
中、闭上眼睛往他面前一站。。。嘿,你还别说,一个比我小点
儿的小丫头,梳着两个小荚荚、瞪着一对儿大眼睛正盯着我呢,
尤其是那张小嘴儿,象滴露的荷花儿,我禁不住身子往前一倾
。。。“滋”的一下觉得满嘴全湿了,所长大人抽笔了!我抢过
笔用力一甩,弄得他满人、满墙,淋漓尽致。
4/2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