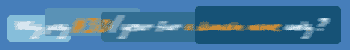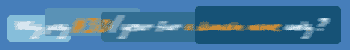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
这坛子和那坛子
霍林河
别的不敢夸口,但要比谁百家饭吃的多,这坛子上能出本人右
者大概不多:六个月基本路线教育、三个月割资本主义尾巴,
每天三顿派饭,一顿换一家,算算吃了多少家!
百家饭好听不好吃,这到不是怕脏,本人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娇
气本来不多。再者说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垄沟儿里捡了一天
的豆包儿,饭还能有脏的?我怕百家饭是因为那个酱!
东北庄稼院儿人家儿大多自己做酱,场院里打好的黄豆,上风
头儿好的分给各家作菜豆,中间的拉去交公粮,下风头儿捡瘪
的、碎的喂马,剩下的就是酱豆了。当然,如果不巧上边蹲点
儿干部在场,那上风头儿和中间的就得调个个儿。
酱的作法很简单,入冬后把黄豆炒熟、碾碎,压成四寸见方儿
的块儿,叫酱块儿,酱块子脑袋一词就出于此,把酱块儿放在
阴凉处,第二年春天种麦子的时候,把阴干、长满绿毛的酱块
儿洗净、捣碎,放在坛子里,加上水和盐、盖好,放在朝阳处
,每天搅几遍,个把月后就成了。
家家的酱都这个作法,一个井的水、一片地的豆,甚至炒豆烧
的豆枝儿都是一辆马车拉来的,可这百家的酱偏偏就有百家的
味儿,绝对不重复。谁家的酱好吃,永远没个公论,因为自家
的酱只自家吃来顺口,别人的酱吃惯了还行,头一口儿没个吃。
偏偏小葱、白菜、香菜沾大酱,加上香喷儿喷儿的小米饭,又
是本人这副穷肚子的最爱,这一顿一换的派饭可就苦了。混熟
了以后还好些,队里的保管员一早儿就会跟我说:“唉,今天
张二寡妇、赵瞎子和王麻子家的酱都是从县里打的,去吧,没
事儿”。说来也怪,县里卖的酱谁吃都顺口,虽然那是孱了一
半儿的苞米作成的。
你说我们这坛子象不象那酱坛子。不敢说这儿的贴子就一定好
,别的坛子的贴子也是这么沾的,可读起来那感觉就是不一样
,一家贴子一个味儿,只有自家的才贴心。外来的一开始看不
惯咱家的贴,说两句也在理儿。想到这儿,觉得两天前回火红
木棉的几贴似有失厚道。希望火红木棉今后还常来,你那派饭
的两毛钱就不收了,四两粮票也免了。只希望这坛子的酱有一
天也会对你的口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