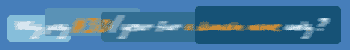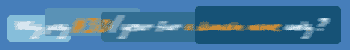为了避免误会,先解释一下本文的名字。这里的“代表”是名词,不是那个时态和语气都含糊不清,进而使句子也失去了定义的动词。这里说的是本人接触过的两个人民代表和一个民意代表。人民代表和民意代表一字之差、含义不同。用通俗的话说,人民代表是选样,就象蔬菜展览会上选蔬菜一样,黄瓜、豆角、土豆、茄子、辣椒,哪样都要有几个。选人民代表吗,就是在人民各阶层中,选出里里外外咋看都象人民的人,参加会议、举手表决,那一双双高悬过霸主鞭的手一举,别说通过的是上头儿早就定下的法案,就是通过的是无字的法案,你能说它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民意代表吗,强调的只是民意。就象蔬菜博览会上的讲解员一样,他不是茄子,也不是辣椒,但是他了解包括茄子、辣椒在内的各种蔬菜的生长、品味和营养特性。这民意代表自己长得象不象人民,甚至是不是人民都不打紧,只要他能把民意放到法案中就成了。(一) 民意代表:联邦众议员布朗那是我刚来那年,一位中国同学的妻子办探亲签证,三次赴京,三次拒签。实验室的秘书建议他去找当地选区的国会众议员布朗,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为了仗胆儿,也是为了把两个半吊子英文凑到一起能把话说清楚点儿,他死拉硬拽地要我和他一起去。我劝他说:“得了吧,哥们,别听秘书瞎逗,人家国家领导日理万机,你又不是选民,他还会管你这点儿事?”他回说了,管他的呢,就当着去见识见识也行啊。嗨,真还别说,小子知道我爱热闹,就用这“见识见识”几个字把我的魂儿给勾活了。行!通过电话约好了时间,两天后的下午一点半,布朗众议员招见。他的秘书让我的同学把有关的材料先传过去一份。两天后我们俩开着他的老爷车按时赶到。先是女秘书接待我们,她微笑着(假的!)先让我们俩坐下,然后自己坐下来打开文件夹说:“你的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交给众议员先生了,他一会儿就与你们谈。他很忙,只能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秘书说完就走进里面的办公室,参议员布朗先生随后就出来了。呵,看那德行:发型整齐,藏蓝色的西装配上一副深红色、带白点儿的领带。隔着桌子,没看清穿的什么鞋,但是我敢肯定,绝对不是沾着牛屎的。我一下子心就凉了半截:这种人还能为人民办事?哥俩儿还没愣过神儿来,布朗就探过身子、隔着桌子把手伸过来了,并自我介绍说:“我叫乔治·布朗,是本选区的国会众议员。”看着我们落坐之后,他才坐下,并接着说:“我的秘书已经向我介绍了你的情况。签证问题归政府的行政部门负责,作为立法机构的议员,我无权干涉领事馆的工作。”得,打官腔了,没戏,我和我的同学心里都这么想。“不过,”布朗接着说,“秘书说你妻子的材料齐全,按照签证条例,领事馆应该发给她签证。我让秘书明天给领事馆发个电传,代你询问一下拒签的原因。”听我们连连说了两声谢谢之后,他又补充一句“我能做的只是询问拒签的原因,领事馆有责任答复我的询问,但是我不能要求他们给你妻子发签证。两天后给你答复。”就这么几句话就完了?他站起来之后,又顺便说了一句:“你们那个试验室,对国家科学研究和本社区的发展都很重要,我在国会刚刚通过的拨款法案上投了赞成票。希望下次选举之后本人还能有幸为本选区、为你们服务。”本来就没抱着希望来,回去以后自然也没有什么失望。出乎意料的是,两天以后,布朗的秘书给我的同学来了一个电话,说领事馆让他妻子再去一趟。后来签证还真的办成了。我对他说,还真该谢谢布朗先生,可他却说“谢啥?政客就是政客,你当他真关心我不成,他是为了竞选时我能给他拉几票!当然了,我的忙他还是帮了,这叫选举能使鬼推磨。”(二) 人民代表:老纪经过七、八年的动乱之后,四届人大要召开了。县里的人都传说老纪当上人大代表了。这可是和中央领导同桌吃饭、一起开会的勾当,提起这事儿,大家眼珠子都瞪得老大。头三届人大代表是怎么选的,我不知道。只是影影绰绰的记得父亲好象有个选民证,大人的事儿,小孩子不知道,父亲的选民证是不是用来选代表的,自然我也不晓得。但是这次人大代表的选择(不是选举)肯定和选民证没关。上头儿说了,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选代表开会这样具体的事儿,哪能让主子亲自操心,由公仆代劳就是了。你看啊,封建社会皇帝是主子的时候,国家的大小事宜,都由奴才(大臣)们先拟好奏折,主子只要“钦此”就行了。新社会人民做主、彻底解放,索性连“钦此”都免了,公仆全包。这次选代表是中央直接下的名额和条件,由县里按条件找人。据说红头儿文件里指定的全县唯一的代表的条件共有八条:(1) 男性,(2) 非党员,(3) 有二十五年以上工龄,(4) 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5) 雇农成份,(6) 至少连续三年是五好,(7) 少数民族,(8)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县委、县革委会拿着这七条,用排除法找人,嘿,正正好好,最后就木工厂老纪一个人符合条件,第八条还超了标准──老纪不识字。过去说上头儿伟大、英明、正确,可都是耳闻,虚!这次可见着了,实!就是西藏找转世活佛,也没这么可丁可卯的,国家领导在数千里之外,人家就知道咱这儿有个老纪,就知道老纪是个地地道道的人民代表的材料!谁要说老纪不象人民,那就一定是昧着良心说话,有诗为证:一脸憨厚汗水淌两手老茧木屑香借问神州谁得似可怜永贵依农装老纪快六十了,没娶过媳妇。解放后,妓女从良、和尚还俗时,政府曾经把一个窑姐儿介绍给他,可是相看了之后,人家说他缺心眼,不同意。后来窑姐儿改配了一个还俗的和尚,而打那之后老纪也就没有再相过亲。自打满洲国的时候,老纪就在木工厂当学徒,学了整整三年之后,拉锯还是走不了直道儿,后来就改看大门儿了。在木工厂里,老纪最为人称道的两点,是他的坚守岗位和大公无私。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厂子全部停工,可老纪还是天天坚持上班,风雨不误。一次造反派开着车到木工厂拉木材,上了子儿的枪都顶到脑瓜门儿上了,老纪就是不给开门,咋地?没发票。老纪的家就在厂子对过儿,坐在门卫室里,透过窗户,家里的事儿就能看个一清二楚,可几十年中,他除了中午回家吃饭,上班时间从来没回过一次家。那年冬天,老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上厕所时脚一滑,一条腿掉到厕所里,骨折了。邻居赶快跑到厂里告诉老纪,让他快去厕所里把老太太扶出来,送医院里瞧瞧。老纪是横竖不肯回去,说家天大的事儿也是小事,厂子里再小的事儿也是大事儿,他不能离开革命岗位。就是厂领导出面,死拉硬劝让他回去看看,也是不顶事儿。最后没有办法,厂长只好派两个女工,把老太太从厕所里扶出来,送进了医院。提到老纪的大公无私,人们最乐道的,是他不沾公家一滴水的故事。那年头儿会议多,一到开全厂职工大会时,厂部里的那两个热水瓶就不够用了。每次开会,都是老纪把自己家里的两个竹皮子暖瓶拿来,白给大夥儿用。怕有人怀疑他借机往家里拿热水,占公家的便宜,每次开完会,他都是打开壶盖儿,两手倒拎着暖壶回家,以示自己滴水不沾、只有一片公心在暖壶的清白。老纪进京开会那天,到火车站送行的,除了县里的党政领导之外,还有几百名手拿花束的中小学生。他回来以后,县里隆重举行了报告会,主会场设在电影院,工厂、机关和学校都设立了分会场,收听大会实况。“嘿,嘿嘿,”坐在主席台麦克风前的老纪显然有些紧张,县委宣传部秘书教他背了几天的台词儿全忘了。有人说了,不对吧,他在北京可是刚刚见过大阵式的。你这就不懂了不是,在那儿,嘴是只管吃饭的,有用的只是一只右手。傻子过年看界比儿的,老纪虽然听不懂那些长篇报告,但是人家都举手时,他就举手,会议中通过了那么多法案,一次都没错过。可是眼下这场景它不一样啊:台下,上千人头晃动,台上灯光耀眼,老纪的脑袋直发晕。恰好儿,县招待所那个梳着两条大辫儿的闺女拿着壶倒水来了,老纪这才忽然得到了启示。“嘿,嘿嘿,大伙都说我是茶壶煮饺子──有嘴儿倒(道)不出来,妈的这回俺可真看到茶壶煮饺子的了。”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缓过了一点儿刚才的紧张劲,接着说到,“你说也真他妈的邪了门儿了,头天儿的宴会吧,桌子中间摆着一个也不知道啥玩意儿做的鸭子,看样子象是好嚼各儿,可你拿筷子去夹吧,又他妈的硬梆梆的戳不动。”台下的人听到这儿,也都觉者有意思,一个个瞪着眼睛、半张着嘴、探着脑袋等下文儿。“赶好儿哇,旁边儿的服务员儿过来了,”老纪用手抿了一下嘴巴,接着说,“人家用手往鸭脖子上他妈的一按──巴答,鸭子屁股后儿就下出一个白精精、水灵灵的小饺子儿来。俺这才明白了是咋回事儿。”这时台上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有些人还巴答巴答嘴儿,好象那珍珠饺子也进了自己的肚子里一样。老纪接下来讲的也都和吃有关,倒是刚刚参加了省里三极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按照省委发的文件,补充了一些人大会议的情况。县委书记讲完之后,又走到主席台上老纪的身边,拉着他站了起来,并抓过他的手,抬高声音说:“同志们,我再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激动的好消息,就是这双长满老茧、普通劳动人们的手,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全国人们代表大会上,代表全县五十万各族革命人民,投下了神圣的一票,真正体现了新社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台上的几个人好象挺激动,台下也响起了一片掌声,希希啦啦的,远远没有听老纪讲鸭壶倒饺子时那么热烈。(三) 人民代表:老何几年以后,选下一届人民代表的时候,由于上头的工作不够细致,给县里找代表的工作造成了麻烦──符合红头儿文件上规定条件的人竟然有三个之多!最后,县委常委会做出决定:卧龙山大队的总支书记老何当代表。究竟县委常委根据什么选定了老何,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按党龄,有的说是按当干部时间的长短,有的说是按文化程度,还有的说是抽签儿决定的。最有意思的一种说法是,县委常委按照西藏选活佛转世灵童的办法,把上届代表老纪用过的竹皮子暖壶、大茶碗还有那顶帽子和其它什杂物件儿放在一起,让三个候选人去拿,结果老何三样全拿对了。那年月堵嘴已经不太容易了,老百姓不知底儿,瞎猜、乱侃总行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不是宪法给我的选举权被无声无息的剥夺了,我还真会投老何一票。我当年下乡的地方,与老何的大队就隔一座山,出于工作上的关系,和他还有点儿私人交往。老何为人豪爽仗义,而又不失机智。他是全公社十二个大队书记中唯一的一个高中生。毕业那年正赶上大学关门,他只好回乡务农,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大队会计,后来就成了二百几十户人家的大队书记。除了公社书记,十里八村知道老何的人最多。具说让他当上人民代表的一个原因,是他敢于和四人帮斗。这是说的玄乎了点儿,可也不是一点儿也不搭嘎,老何的抗上是有名的。那年头,农民都突然变得不知道怎么种地了,从包米的间距,到刨坑儿的深浅,全由上面说了算,整的种地比绣花还费劲,往往误了农时、瞎了地。只有老何的大队不一样。每年他去县里开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之前,都要把几个队长叫来训话:“还是那句老话,哪块儿地种啥、啥时候种,都按老法子,别听上头他妈的瞎咧咧,出了事儿我抗着。”结果是年年春天老何挨批,说他不按毛主席的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种地,对抗党在农村的基本路线。通常吗,老何也不多辩解,总是痛心疾首地检讨,保证来年不再犯错误。有意思的是,他竟然年年能蒙混过关。为啥?公社领导知道,到秋天的时候,卧龙山交的公粮一定最多,那时候老何还会上台,不过角色不同,他将介绍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科学种田的经验。与他的前身老纪不一样,老何个性鲜明,特别是几碗高粱酒下肚后,常有惊人之举。据说一次在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时,晚上多喝了几碗之后,和同一个房间的其他几个大队书记竟然来了一次“定力比赛”:几个人一丝不挂、仰面超天地躺在床上,然后嘴上开荤,看谁能定得住乾坤。老何开会回来的报告我没有听过,但是据听过他报告的人说,他即没提到在会上的抗上之举,也没说过国宾馆里曾经有“定力比赛”。其实老何天生是一个好的民意代表,跟着他进京的要是几十万选民的选票,他也许真的会象对岸的朱高正先生一样,抢过话筒、大骂老贼、为民请命。突然想起老人家一句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刀刃能削刀把吗?9/4/2001 [无奈后的麻木-《三个代表之二》读后]--: 老椰子
[无奈后的麻木-《三个代表之二》读后]--: 老椰子
 [ 杂感“麻木”]--: 大布苏
[ 杂感“麻木”]--: 大布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