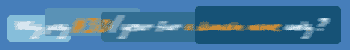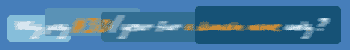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一)
每天都是女儿起来得最早,特别是这几天,由于她还要带两个刚入学的邻居的孩子
一起上学,所以不到 7点就走了。象往日一样,洗漱完毕,和妻子打了一声招呼,
就先出了门,她总是比我晚走十几分钟。在门口穿鞋时,看到手机还挂在墙上,心
里就埋怨女儿粗心,又忘记带上手机了。由于我和妻子的办公室只隔一栋楼,所以
根本就用不到手机,当初买手机就是为了女儿,开始她上学还常带在身边,后来嫌
麻烦而且也很少用到,不提醒她就忘了。
由于星期一在家休息一天,出门的时候有些庸懒──迟来的星期一反应。秋风迎面
袭来,感到一丝凉意、几分萧瑟,心里合计着,是否下周末能约几个朋友去农场采
集果实。在撒满阳光的金色秋季,采摘那一个个丰满的果实,直接享受大地的恩赐,
对我永远是一种特殊的享受。记得小朋友说他们那里有盛产亚洲梨的果园,曾经和
妻算计着什么时候去一次,也顺便看看他们一家。
地铁站口,本区竞选市议员的民主党候选人和市长候选人的支持者在散发传单,撒
满阳光的站台上,经过昨天那场大雨的洗涤,空气显得比平时要新鲜。
在地铁车上读书,对于我不仅仅是消磨时光,而且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特别是想想
能把每天的这些别人浪费的零散时间都利用起来,常常有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今
天读的是《周易》,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农历八月正是公历的九月,
细想一下也有道理,秋季有萧杀之气,二十五年前的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三十年前
的9月13日林彪的飞机坠毁,再过几天就是难忘的9·18了。想到这儿自己也发笑,
怎么也成了阴阳先生了?其实九月的上半月多半只是农历的七月下旬,再说这近几
年的九月就没有什么大事。
8点55分,走出2号和3号地铁的华尔街站,街上似乎与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地
面上撒满了碎纸片。“怎么,昨天又是纽约的哪个体育队得冠军了?”这是我的第
一个反应。不对,怎么有一种烧焦的味道?抬头一看,JP摩根办公楼后面,一个尖
顶的大楼上飘着浓密的烟尘。噢,失火了。这时听路边的人在议论,一驾飞机撞到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了。回头一看,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厦的一个,正迷漫着浓密的
烟火。我加快脚步跑到办公室,所有人的计算机都在显示着CNN 播发的图像,有人
说撞楼的飞机是波音737(后来证实是767)。“绝对不是事故!这么好的天气,不可
能发生这样的事故!”罗伯特在喊。“砰!”这时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站在
西北角窗口的几个人同时高喊:“又一驾飞机撞上了!”
(二)
与其他人一样,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给妻子打个电话。那边没有人接,我估计她
可能还在路上。由于没有意识到势态的严重性,我当时并不担心担心她的安全。后
来才知道,她乘坐的地铁在TWC附近的CHAMBER街进站的时候,正是第二个大厦被攻
击的时候,现在想来才有些后怕。
我给她打电话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她弟妹的哥哥就在 WTC的六十几层楼上的一个办
公室工作,正是第二个楼被炸的那几层,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一个楼。上次亲友
会餐的时候,还和他说过找个时间一起出去吃午饭。他的父母是吉大的资深校友、
一位性李的教授,年岁都比较大,我们打电话虽然帮不了什么忙,但总是一个安慰。
可是我手中没有他的电话。正在这时,办公室里有人说,公司在华尔街一号的总部
和巴克利101号办公楼的人员都已经疏散,后者离WTC只有两条街。正在这时,广播
里也传来了人员疏散的通知,大家才慢慢地向电梯和放火通道走去,由于远离现场,
没有什么感到急迫。我问周围的人,是否可以用电梯,回答不一,有的人在那等电
梯,有的人走向防火楼梯。我决定和大多数人一起乘电梯下去。这时约翰跑到电梯
口告诉大家,今天不能工作了,大家直接回家吧。
出来之后,街道上已经充满了人。我经直跑到妻子的办公楼,楼下的大厅里站满了
人,正围在三台大屏幕的电视机前。平时,这几部电视是用来报导股市行情的,虽
然屏幕上仍然显示着纽约三大股市正式交易之前的期货指数,但是已经没有人关心
它们了。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9 点25分。在人群中找不到妻子,我就四处找电话,
这时我才后悔早上出来的时候没有把手机带上。还好,最后在楼里找到了一个电话
亭,还算顺利,电话一拨就通了。我告诉他赶快给李教授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有没
有他儿子的消息。妻说她已经打了,两位老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打开电视
看到了 WTC上浓密的烟火,才开始为儿子的安全担心,他们也不知道儿子在哪个楼
上,只知道是开放观光的那一个。妻子这时说,她也许不应该给老人打电话,没帮
上忙不说,还空让他们的心悬着。我解释说,不能这么说,有人和他们联系也是一
个安慰,再说他们迟早还是会知道的。我告诉她我就在楼下,让她赶快下来。
9点30分,美国总统布什在弗罗里达州发表短暂的电视讲话,宣布美国正受到恐怖
分子的攻击。又过了大约十几分钟,电视上传来了新的画面──华盛顿五角大楼起
火,工作人员正在撤离,白宫中的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华盛顿一个商场失火( 商场
的火与恐怖分子的袭击是否有关,我现在还不清楚)...电视上的文字这时也由
“WTC 受到攻击”改成“美国受到攻击”。人们神色凝重,议论的声音也骤然停止
了。我想在场多数人与我一样,心里都在想着两个更为可怕的字眼:战争。这是一
场恐怖分子对美国不宣而战的战争。
(三)
人们显然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是这里离事发地点 WTC毕竟有一英里之遥,没
有人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妻子说她还要回办公室,看看是否她们公司的员工
也要撤离回家。我说:“也好,你再顺便给李教授打个电话,向他解释一下我们所
看到的情况。我再到公司看一下就回来,还在这儿见面。”当我再回到公司的楼前
时,许多同事已经离开,部分人向港口走去,准备利用渡轮先离开曼哈顿再说,但
是多数人仍然滞留在街上。三五成群的人们在谈论着事件的发展,也有人互相关照
如何离开这里,有手机的人都在忙着打电话,但是很少有人能打通,虽然有几位女
士在哭泣,但是多数人仍然非常冷静。与平时不同的是,在街上找不到一个警察和
保安人员。
看看公司这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便回到妻子办公楼的大厅里。刚刚走进大厅,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隔着玻璃门看出去,整个街道充满了灰白色的烟尘。不知道是
谁喊了一声“又爆炸了!”大厅里的人几乎全都冲了出去。这时整个华尔街几乎全
部被硝烟淹没了,根本看不清硝烟从哪里来。我以为是附近的一个或者多个大楼又
发生了爆炸。“连锁性攻击!”不知道为什么我头脑中闪现了这几个字,那么下一
个目标...想到这我又回到大厅里寻找妻子。找不到她,我只好出来,跑到哈雷
姆河边我们中午常在一起吃饭的地方,看看她是不是在我回来之前就出来了。正在
这时,突然有人喊“看,河上也爆炸了!”放眼望去,只见哈雷姆河面也是一片硝
烟,仔细一看才发现,只是从WTC 冲出来的一条象巨龙一样的烟尘落在河上。一场
虚惊。
我找不到妻子,却看到三个女士在那里站着哭泣、颤抖,我问她们是不是在等人,
其中的一个摇了遥头。我对她们说:“如果不等人的话,最好快点儿离开这,往上
城方向走,那儿比较安全”听了我的话之后,她们便加入了那已经形成的、平静地
向上城方向移动的人龙。她们中的一个回过头来,问我为什么还不走,我说我得等
我的妻子。人群中仍然看不到妻子的影子,我便放开嗓子高喊她的名字。在华尔街
上高喊一个人的名字,要是在平时不知道会引来多少人的奇怪的眼光,可当时连一
个回头的人都没有。
这时才突然想起当时和妻子约定在大厅等候,她会不会还在那儿?想到这我又回到
大厅,一进门就高喊她的名字,她不在,但是却引出了她的一个叫哈威的中国同事,
看见他浑身厚厚的烟尘,通红的双眼,把我吓了一跳。他一面揉着眼睛,一面用手
指着烟尘多的方向说:“你妻子在外面找你,好象往那面跑去了。”我跑出大厅,
也向那个方向跑去,正好与又跑回来的妻子撞个正着。俩人静下来之后,才弄清楚,
原来不是附近发生了任何爆炸,烟尘来自倒塌的WTC2号楼。
(四)
又是一场虚惊。原来她在回到办公室以后,按照老板的要求把公司员工的电话号打
出来一份,接着就给李教授打电话,他们正在为儿子的安全担心。电话还没有打完,
就传来了WTC2号楼坍塌造成的巨响,窗外迷漫着硝盐,办公室里没有人知道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情,她的老板高声喊着让人们立即全部离开。她放下电话冲出办公室的
时候,也正是我在楼下冲出大厅的时候。
看着妻子身上的灰尘,我边替她打扫边说:“你为什么往那边跑?河边才是比较安
全的地方吗。”她回答说:“每天中午吃饭时,我不都是在那里等你吗?”我沉默
了一会儿说:“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发生,谁也别找谁,自己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再
说...”“那哪行。”没等我说完,她就打断了我的话。我告诉她,这是最好的
办法,再说,如果我们都出了事儿,孩子怎么办。提起孩子,不免又有些担心,虽
然她的学校离出事地点很远,安全不应该有问题,但是交通混乱,她可怎么回家呢?
想到这儿,又后悔早上没有叮嘱她带上手机。
我们商量着应该给不住在下城的朋友打个电话,一是告诉一下我们的情况,二是让
他们常给我们家打打电话,免得孩子先于我们到家而着急。我在离开办公室之前,
给老椰子的办公室打了一次电话,但是他不在。当时能记住的只有孙亮的电话,但
是几个电话亭都排着长队。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尽快离开这里最重要。
路面上塞满了车,公共汽车、出租车都坐满了人。在这种情况下,地铁一定已经关
闭,就是不关闭也不能去乘坐它。所以我们就加入了那群灰头土脸,但是却非常冷
静地向上城(北)方向移动的人群。
这时我才感到在烟尘的刺激下,嗓子发痒、发干,妻子递过来一张润湿的纸巾──
她竟然记着带出一瓶水出来!路边的商家也有人站在那不断向路人递来纸巾和水,
冷酷的纽约人表现了少有的人情味。
一路上,除了惦记孩子,几乎什么也没说。走到中国城的时候,又听到了一声闷响。
回头望去,WTC 的位置只有一片浓烟。我们都没带手表,问了一个过路的人,时间
大约是10点30分左右。虽然看不清楚,但是每一个人都已经猜到,一定是WTC 的第
二个楼也倒下了。当时我们不知道两个楼是否是受到了新的攻击才倒下的。
看着那片浓烟,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原子弹爆炸的蘑菇状烟云。记得小的时候,觉
得那些烟云是那么的美丽,因为它代表的是祖国的强大与骄傲。而现在却充满了恐
惧,人类竟然有如此丑恶的一面!如果 WTC上空的那片烟云是原子弹的烟雾,而不
是现在看到的汽油燃烧的火焰,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这是我第一次理智地把这次
事件与人的生命联想起来。
(五)
任何事情只要和生命联系起来,就无法想得、谈得那么轻松了。尤其是在当你离它
那么近,涉及的又是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时候,甚至连理智、理想以及复仇的欲望也
都变得那么苍白无力。那些压在坍塌双塔废墟中的、可能数以万计的人,今天早晨
也可能象我一样、象在每一个和平的早晨一样,在出门的时候,对妻子、丈夫、儿
女、父母和兄弟姐妹,或者其他的亲人和朋友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不同的是,他
们永远的走了。
我们跟随着人流继续向前走去,这时下城的曼哈顿桥、威廉姆斯桥上面已经充满了
步行的人们,我有些为他们担心。正好前面有一辆公共汽车停下了,跑过去一看,
居然还有座位,上去以后,妻子问司机车往哪里开,他回答说:“还能去哪里?上
城。”司机一只手扶着方向盘,一只手向人们挥舞着说不要票了。
虽然汽车并不比走路快多少,但是能有个座位坐着当然舒服多了。后面车门口的台
阶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身上、头上的粉尘至少有一毫米厚,手上还有轻微的伤痕。
旁边蹲着一位妇女把润湿的纸巾递给她,她接过来只是攥在手里,然后还是呆呆地
坐在那儿。到下一站的时候,才知道那个一直蹲着照料她的人与她并不认识。
人在紧张的时候,时间的感觉就不那么敏感了,不知不觉地,汽车已经爬到了(对,
爬是最恰当的描述)37街。这里是终点站。
下车没走几条街就是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了。虽然在纽约已经居住了十几年,但也只
是陪着来访的朋友来过这里两次。要是在平时,我一定会驻足看看,我喜欢那些在
阳光照射下随着微风轻轻飘动的各国的国旗,它们使我连想到人类的理智与和平。
而现在对她却连躲都怕来不及了。这时才突然想到,十几年的时间里,竟然从来没
有登上过WTC的观光台,总是想着以后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没想到... 联合国
总部门前的人行道已经关闭了,我们也随着人群在另外一侧绕了过去。
在第二大道的45街于50街之间,我们又挤上了一辆往上城的公共汽车,这次是真正
挤上去的,车上站满了人。不过乘客中已经没有多少灰尘蒙面的了,司机的态度也
回到了真正纽约味儿。我们问他这辆车往那里开,他只是冷冷的回一句:“你告诉
我往哪去吧。”倒是旁边的一位黑人妇女告诉我们是去125街。
这次汽车比爬的还慢。我们前面是一位在美林证券公司工作的老太太,说她也曾经
亲眼目睹过93年那次爆炸事件,但是没有任何事情能与这次相比,真是惨不忍睹。
当我们谈到正在为女儿担心时,旁边的一位老太太劝我们不要担心,说女儿的学校
远离出事地点,另外学校也会很好地照顾她们的。她还说她自己就在中国城的一个
学校教学,爆炸发生后,学生们就有组织的疏散了。无论你是多么自信的人,在这
种情况下,别人的分析也是一种安慰。后来在谈到什么人可能是制造这次灾难的恐
怖分子时,两位老人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在美林证券公司工作的老太太一口
咬定是阿拉伯人干的,那个小学的老师却说不能过早下结论。
汽车除了在中途的一个车站为了让一个坐轮椅的乘客上车而停了一次以外,一直开
到79街。
中城的曼哈顿,除了偶尔有几个身上仍然覆盖着灰尘的行人之外,看不到一点儿灾
难的影响。司机在广播中宣布,客车将直接开到125 街,中间不停。考虑到这种时
候哈雷区可能不太安全,我们决定就在这里下车,然后转车、坐出租车或者走回去。
(六)
下车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看看孩子回来没有。她们的学校虽
然远离事发地点,但是这样的大事,即使仅仅是心理上的冲击,对于孩子们也是难
以承受的。
周围的电话亭都排满了长队,我又在后悔早晨没有把手机带上。这时看到路边一家
洗衣店,店主好象是中国人,我和妻子就走进去问是否可以借电话用一下,她毫不
犹豫地把电话递了过来,听见收音机里的播音,才知道她是韩国人。电话是接通了,
但是女儿不在家,我们开始有些担心。
出租车还是很难找,公共汽车又迟迟不来。后来才知道横穿中央公园的汽车都取消
了,我们决定步行走回去。
坐落在59街与110 街的中央公园,是纽约人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场所。在风和日丽的
夏天,各种各样的体育场中、自行车道和跑道上都会充满锻炼身体的人们。有在树
阴下牵着狗散步的女士,有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的老人,有趴在草坪上读书的学生,
也有许多少男少女躺在地上沐浴着阳光。但是,现在公园中的人却格外稀少,行人
虽然还可以自由出入,所有行驶汽车的出入口却都被警察拦住了,敞着门的警车里
传来新闻播音员的实地报道,周围零零散散的站着一些聆听的人们。
静,中央公园里今天格外的静。
走上了阿姆斯特丹大道,远远就听到了圣约翰天主教教堂不停的钟声,那是对死难
者的祷告。一家医院的门口,排着长长的自愿献血的人。
下午2点20 分,经过足足四个小时,终于回家了。这时才感到劳累和后怕,打开窗
户,远远望着下城方向已经与天空的云混成一体的浓烟,第一次感到纽约也是自己
的家园,第一次感到她在我生活中的分量,是她为我遮蔽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然
而现在她却无法给我家的安全感。
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国内的亲人打电话,报个平安,我不想让他们早晨起来看到电视
上的恐怖画面时为我们担忧。当然也忘不了向吉坛报个到,因为那里有正在为我担
心的朋友。接着就是连续不断的电话,远的、近的、老朋友、新相识,充满了关怀
和温暖。
这时电视上传来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鸣枪庆祝的画面,心里又生起一阵阵的疼
痛。冤有头、债有主。以数百人的生命当炸弹,把上万无辜的人葬送在废墟之下,
真的就那么值得庆祝吗?民族偏见使我做出这样的设想:以善良为美德的中国人就
不会有这样的举动。然而读了网上许多论坛的文章之后,才知道自己错了。
“纽约人引为骄傲的双塔毁灭了,纽约人的视野从此将彻底改变。”电视播音员一
语双关的说。是阿,但是这次事件改变的何止是纽约人的视野,也许它将改变整个
人类的命运。
我相信,勤劳的纽约人会在WTC 的废墟上建起新的双塔,然而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
整个人类会象浴火的凤凰,在废墟中得到新生吗?
突然感到需要一个上帝,但不是那个自称全能,但是却把全部邪恶和丑行的责任推
给人类的上帝。我需要一个能够唤起人类聪明、智慧和善良的上帝,也许她就在你
和我的心中。
(全文完)
9/14/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