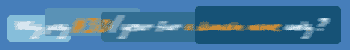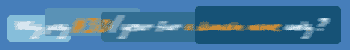一个人和一部车一样,时间久了,有些部件的功能就要退化,需要修理。此为自然
法则。不管这个世界是谁整出来的,神创的也好,偶然形成的也好,这个法则确确
实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一个无情的客观存在。
今天翻出日记读,发现一组二十一年前在医大一院病房里写的东西。这是一个二十
多岁的学生眼中的人世间的一个角落,一个苦难的角落。
十一月三十日
毫无疑问,死亡对于人是个可怕的东西。我相信,肯定有人在某种情况下,会把生
死等同地看待,甚至把死亡看得更为需要。但这些是特例。
现在,我坐在一间病房里。这里,住着一些患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在他们那
里,我看到了死亡对人的压迫,也看到了人对死亡的反抗。
垂危的人的精神世界,未有经历的人是无法准确地了解的。他们现在是人群中的弱
者,就象青青的草原上的一些半枯的草。但是,和草不同,病人是有思维的人,他
们能预知那可能会到来的不幸。这种精神上的附加物往往会加速这个不幸的到来。
然而,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康复的希望,这希望是一种本能的野心,使人去和命
运挑战,推迟这个不幸的到来。
十二月二日
整个一周过去了,父亲的病情没有多大改善,可以说是有些转机然后又有些反复。
在他兴致好的时候,能同别人谈点儿话,但内容多半是不连贯的。可是,当他谈到
发生时间很久的事情时,却显得惊人的清晰。对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他津津乐道。他
讲到吴大舌头进北京开会,念一首诗:小弟吴俊升,初次到北京;到此来开会,全
靠大诸兄。
我说:这是什么破诗啊?你儿子写的比这强多了。还亏你记住了,在我读过的文字
资料中从没见过。
父亲说:就是说说俏皮话吧,哪能上什么文献!这些军阀多数没什么文化。。。
对于家族的过去,他也谈了很多。他特别提起那位在通化失踪的弟弟,也就是我的
叔叔,语言、表情中蕴含着深厚的兄弟情谊。他执意不排除这位弟弟仍然活在人间
的可能,虽然他更相信此人已在与日本兵的激战中战死。
他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兴致不好,体力很衰弱,精神很疲倦。我们姐弟轮流着,默默
地守在他身旁。
十二月四日
把一个人的胸腔锯一个方洞,然后掀起血淋淋的肉骨头,伸进一只手去按摩心脏。
对于普通人,说起来是恐怖,亲眼目睹则是震憾。
这个惨象就发生在离父亲的病床几尺远的临床。我必须站在那里,用身体挡住父亲
的视线,所以我不得不就这样近距离接受感官和心灵的刺激。
十几分钟以前,他还提起想抽一支烟。看来神志非常清楚。
他也许预感到他马上就要死了,在最后的一阵喘息之间,眼里涌出了泪水,吐露了
他对人生的留恋。活着的人真是要珍惜生活啊!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去看看那些
垂死的人吧!
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呼吸开始减弱;他慢慢地停至了呼吸,身体开始冷却。他死
了。他死于凶残的心藏病。
十二月五日
来病房接我班的老姐(最小的姐姐)心疼我,把连夜收拾好的几个猪爪煮好带来。
那是家传的一味美食,别人做不出来的。
我说:姐呀,你饶了我吧!我十天半月之内可能没法吃肉。。。
十二月九日
我已在这个病房里的小凳子上度过十四个下午和一些晚上了。今天,我觉得特别难
受,全身每一个地方都难受。我想,我也许是感冒了,也许是过于疲劳了,也许是
两者都有。
十二月十三日
是的,我是感冒了,而且挺严重的,发高烧。十号这天早上,很严重的症状表现了
出来。不过,病房护理工作也恰好在这时结束:父亲的状况大大改善,可以出院回
家静养了。
那个以后可能要伴我一生的人把我接到她家。我结束了料理病人的日子,又开始了
作为病人被人料理的日子。我一般病不倒,倒了就很重了。我在她那里整整躺了三
天,今天爬起来上课,仍然昏昏沉沉的。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日于纽约